陈子善:藏书票,书斋长物
《藏书票之话》是日本斋藤昌三所著。书前有日本近代旅游文学创始人小岛乌水(1873—1948)序、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1858—1933)博士英文序和作者自序。正文三章十一节,即首章五节:前言、藏书票的主旨、制作的种类、贴附的位置、制作的准备;次章三节:藏书票的起源、日本藏书票史、装帧与藏书票;第三章三节:藏书票爱好者与收集趣味、日本藏票界领袖与藏票会、藏书票制作者;附录四篇:日本藏票会作品概评、藏票同好会作品、冈崎藏票会作品以及藏书票余谈。书末又有藏书票图录,共收欧美和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藏书票代表作百余种,包括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作家雨果和夏目漱石、画家马奈和比亚兹莱等世界文化名人和斋藤昌三自己使用或制作的藏书票,每页一种,洋洋大观,其中日本大正至昭和初期的藏书票20余种为原拓贴入,尤为珍贵。

《藏书票之话》封面
由东京文艺市场社于1929年8月6日初版的这部《藏书票之话》为16开本,用纸和装帧极为考究。全书分别选用法国纯云石(花纹)纸、奥地利黑色罗纱纸、西班牙安达鲁纸、英国和德国纯质厚纸以及日本和纸精印合订,小羊皮精装,书顶、书脊印有EX LIBRIS(即拉丁文藏书票之意)字样,封面书名烫金且饰以彩纹。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12部为作者自存本,另外488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在斋藤昌三多达70余种各类编著中,这部《藏书票之话》是最为华美、气派的一种。
众所周知,藏书票源远流长,起始于15世纪的德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达到黄金时期,是西方书籍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东方的藏书印艺术同旨异趣,互相辉映。据斋藤昌三在此书中考证,早在明治初年(1868),藏书票就已流传到日本,明治五年(1872)日本出现第一张纯西洋风格铜版蚀雕藏书票,到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月,诗刊《明星》创刊号上发表了佚名所作较为详细的介绍藏书票的文字。从此以后,藏书票在日本文坛和藏书界得到认同和广泛使用。夏目漱石、田山花袋、北原白秋、内田鲁庵、小岛乌水、日夏耿之介、川路柳红、志贺直哉等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大家都成了藏书票爱好者,桥口五叶、木村庄八、石井松亭、竹久梦二、有岛生马等著名画家也都成了藏书票作者。但提倡和推广藏书票最力者还是斋藤昌三,这部集欧美和日本早期藏书票之大成、堪称简明藏书票史的《藏书票之话》就是一个明证。笔者不知道西方最早研究藏书票的专著出版于何时,《藏书票之话》却是日本同时也是东方最早研究藏书票的专著,比我国梁栋、鹏程先生编著的《藏书票艺术》一书早问世60余年之久,难怪日本藏书界要奉之为藏书票“圣经”。

1929年初版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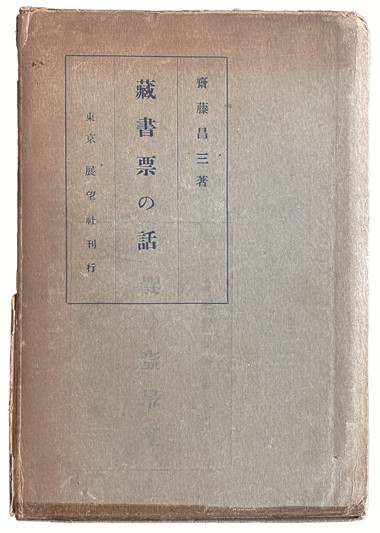
1930年改版本函套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与这部藏书票“圣经”有着特殊的因缘。首先,鲁迅曾购读《藏书票之话》。1930年6月13日鲁迅日记记云:“夜至内山书店买《藏书票之话》一本,十元。”十元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鲁迅购置的已不是初版本,而是1930年4月日本展望社的改订增补版。《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出书后大受欢迎,不到半年即被抢购一空,而初版本又有一些错字,如书脊所印“EX LIBRIS”误作“EX LIBLIS”,因此才有再出改版本之举。尽管改版本无论用纸还是装帧都不及初版本,但“做了些许增补”等,使之更为完备,正如斋藤在《再版序》中所指出的:“比之前版趣味独具。”鲁迅对斋藤昌三的编著一直很注意,斋藤昌三编印的日本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内田鲁庵的书话集《纸鱼繁昌记》(1932年2月书物展望社普及版925号)、《续纸鱼繁昌记》(1934年书物展望社限定版916号)和《读书放浪》(1932年书物展望社限定版153号),鲁迅都有收藏。直到逝世前一个多月的1936年9月8日,鲁迅还购买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1936年5月书物展望社决定版490号)。鲁迅的藏书票知识是否由《藏书票之话》而来,尚不能遽下判断,但由此足可窥见鲁迅对藏书票和日本书话著作的浓厚兴趣。
其次是书话家叶灵凤。1932年至1933年间,热衷搜集日本藏书票和有关文献的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灵凤先后为斋藤昌三写过四篇书话,即同题《纸鱼繁昌记》的两篇、《书斋之成长》和《书斋随步》,两位爱书家交流切磋、互通有无的深厚友情在这些亲切醇厚的文字中表露无遗。即使在日中交恶的非常时期,两人的情谊也未中断,斋藤昌三还辗转托人赠叶灵凤新制的藏书票多种和《纸鱼繁昌记》改版本,不能不令人感动。
必须指出的是,据作家傅彦长的日记,1933年8月9日,叶灵凤在寓所请巴金、施蛰存、林徽音、杜衡等友人观赏藏书票,应该就包括这本珍贵的《藏书票之话》在内。三个多月后,叶灵凤在1933年12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长文《藏书票之话》,这是中国第一篇,也是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较为权威的一篇探讨藏书票历史和艺术特色的文章,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是几乎一字不改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还有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20世纪60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此文后收入黄俊东的第二本书话集《猎书小记》(1978年香港明窗出版社初版),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然而,无论是鲁迅,还是叶灵凤和黄俊东,这三位《藏书票之话》的中国收藏者,对其作者斋藤昌三的生平和众多文学贡献都不甚了了。20世纪50年代后,叶灵凤好像和斋藤昌三失去联系,斋藤昌三去世,叶灵凤大概也不知道,否则他是决不会不为文纪念的。
斋藤昌三系日本神奈川县人,原名政三,笔名未鸣、桃哉,藏书室名“少雨庄”,晚年自号“少雨叟”。斋藤早年服务于商界,曾在邮电局、建筑局和贸易公司任职,但他迷恋文史,尤其爱书如命,以搜集初版本、限定本、私刊本、查禁本和藏书票为己任,为当时收藏和研究明治、大正时代稀见书刊的三大“书痴”之一。
后来他转入文坛,先后担任《书物往来》《爱书趣味》《芋蔓》《怪诞》杂志和《明治文艺侧面钞》《明治文化全集》等书的编辑。1931年7月,又与日本著名藏书家庄司浅水、柳田泉等人合作创办书物展望社,出版《书物展望》杂志和书物展望社文学丛书120余种。其中有德富苏峰的《成篑堂闲记》《小林多喜二随笔集》、横光利一的《上海》、新村出的《典籍散语》以及坪内逍遥、内田鲁庵、长塚节、北原白秋、柳田国男、土岐善磨、斋藤茂吉、木村毅、佐藤春夫等名作家的著作,不但开日本近代读书杂志和书话作品出版的先声,而且以装帧典雅大方、颇具日本传统艺术特色而享盛誉,被称之为日本近代出版史上的“书物展望时代”,也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斋藤昌三晚年主持《书痴往来》杂志,并任茅崎市立图书馆名誉馆长。他著作等身,除了代表作《藏书票之话》和上文提到的《纸鱼供养》《书斋随步》等书外,还有书话集《书痴散步》《书国巡礼记》《书淫行状记》《银鱼部队》《纸鱼地狱》《书物志展望》《艺天杂志之话》《东亚软书考》和《现代日本文学大年表》《现代日本笔祸文献史》《好色家三十六人》等,殁后出版了五卷本《斋藤昌三著作集》。
讲谈社《日本近代文学大辞典》给他的头衔是“书物研究家”,确切地说,他是藏书家、版本学家、书话家、藏书票研究家、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家和性学家。在这么多的领域里,斋藤昌三都有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的日本文化史上,斋藤昌三可算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十分难得。荷兰高罗佩如果结识他,很可能会写出《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姊妹篇《日本近世房内考》。
叶灵凤说得好,对书籍没有爱恋的人,是毋需所谓藏书票的。小小的藏书票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却甚大,在我看来,是超过中国传统的藏书印的,至少各有所长。它不仅是书斋长物,亦是表扬爱书人个性、趣味和见解而守护着他的珍藏的小装饰,西方的神话、宗教、文字、典故、文学、美术、音乐、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纹章、自然、生物、民俗、建筑、人体、性爱等,都在方寸之间,有生动、细腻、别致的表现。一部藏书票演变史,其实也是独特又形象的微型西方文化发展史,这也就是藏书票虽为“小众艺术”,却很值得欣赏、把玩和研究的原因。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蜂拥而入,“纸上宝石”藏书票也随即而至,并很快与日本传统艺术如浮世绘版画等相融合,“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斋藤昌三这部《藏书票之话》就真实展示了这个藏书票东渐的过程,为东西方之间这个细小却很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留下宝贵记录,更进而对中国的藏书票兴起和流布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藏书票之话》的价值已超出了藏书票研究本身,从文化研究的层面考察,它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称之为东方藏书票“圣经”是名副其实。
初版或限定版的斋藤昌三书话著作早已成了日本爱书人竞相搜集的珍籍,《藏书票之话》无论初版还是再版本,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连日本许多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未收藏。我1997年游学日本时,曾浏览了90年代日本各大旧书店书目,只有1994年东京《庆文堂古书目录》第58号上出现过这部藏书票“圣经”初版本,不知被哪位幸运者购去。与此同时,对斋藤昌三和《藏书票之话》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历史悠久的《学镫》《日本古书通信》和《日本藏书票》等杂志经常发表从不同角度探讨《藏书票之话》的文章,连为之作序的小岛乌水、斯塔尔博士和书中提到的日本早期藏书票爱好者的生平和收藏也成了研究对象。
在我们中国,鲁迅收藏的《藏书票之话》改版本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叶灵凤的《藏书票之话》先归北京一位受人尊敬的爱书家所有,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而黄俊东的《藏书票之话》在借出之后失去,令其痛心不已。我也有幸在大阪天地书房购得一部书品完好的《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113)。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拥有这部东方藏书票“圣经”的朋友应该又有所增加。这当然是大好事。
然而,对广大藏书票爱好者而言,还是难以一睹此书真容。因此,当我得知魏大海先生翻译的《藏书票之话》即将出版,不禁欣喜万分。这部《藏书票之话》在问世92年之后,终于有了中译本,实在是中国爱书人和藏书票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更可进一步为东方藏书票研究史作证,为中日文化交流史补缺。故我乐意为之写下这些话以为贺,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 陈子善:梅川书舍札记[2022-02-16]
- 陈子善:“徐志摩拜年”[2022-01-30]
- 张春田: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传统[2022-01-20]
- 音符中的心有灵犀:现代作家与古典音乐札记[202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