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当代小说需要“革命”
王尧近日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民谣》。他称之为“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二十年前写下开头,直到去年的某一天,他又突然涌起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是,他在疫情下闭锁家中的几个月时间里,集中精力完成了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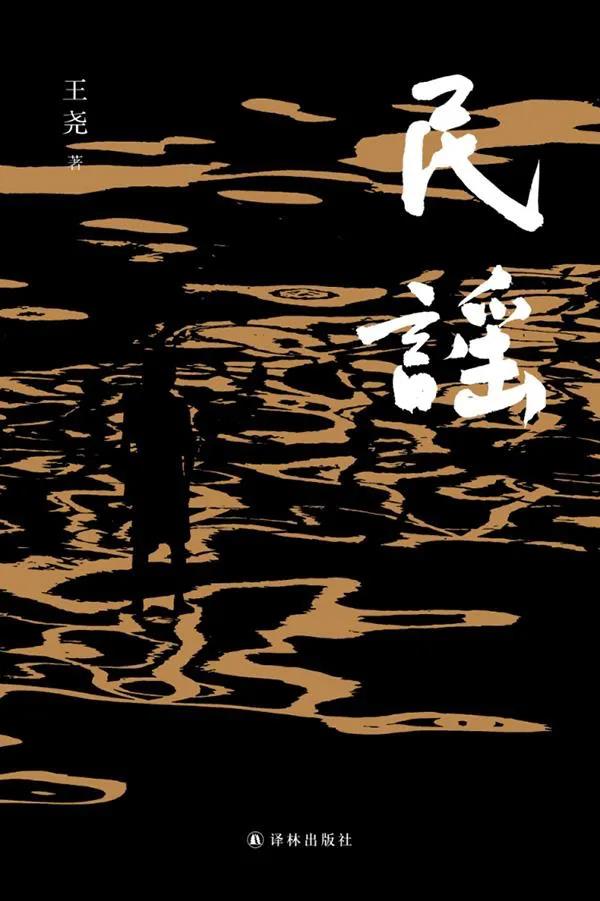
《民谣》,王尧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第一版,58.00元
作为苏州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尧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作为散文家,他数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在多种报刊上开设专栏,出版有《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多种散文随笔集。现在,王尧作为小说家出场了。

王尧
作为批评家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评论的?
王尧:我应该是出道比较晚的所谓批评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研究,在当代文学史领域沉潜了许多年,我的许多批评家朋友风生水起时,我还在当代文学的“故纸堆”里。所以,我很赞成把当代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个部分,当然这两部分是相通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才用了部分精力做文学批评。这样一种先文学史研究、后文学批评的出场方式,对我自己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自己做导师了,我一直鼓励学生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者兼顾。
中华读书报:2001年,您和《当代作家评论》联合主办“小说家讲坛”,策划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您是较早开始和中国作家对话的评论家,为什么您这么重视对话?
王尧:在策划“小说家讲坛”之前,我在台湾东吴大学做了半年客座教授,访谈了余光中、陈映真、黄春明先生等。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对话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有独特的价值。2001年6月从台北回来后,应《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之邀,我和莫言在大连相会,我们仨聊了文学创作,我建议可以合作做一个“小说家讲坛”:小说家在学校演讲,《当代作家评论》发表小说家演讲以及我和小说家的对话。这个讲坛持续了好几年,曾经是文学界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和作家的对话,后来以《在汉语中出生入死》为书名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对话的作家朋友,都觉得意犹未尽,我又在苏州大学出版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十本。现在看来,这套书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料。那几年,我几乎集中精力做这件事。在我看来,了解和理解作家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之一,而对话则是了解和理解作家的方式之一。我长期在大学工作,自然会思考文学教育的一些问题,“小说家讲坛”实际上也建构了一种文学教育的现场。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对话对于评论有怎样的启示和帮助?
王尧:受益很多。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与批评家区别很大。这一代作家读书很多,和批评家一样有学养,他们对小说本身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批评家。对小说的艺术感觉和对小说的意义阐释同样重要,前者往往是批评家的弱点。对话让我更坚定了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想法和实践。我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写小说的想法,与当初的对话关系很大。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访问作家、编辑家、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等,就“新时期文学”做了各种口述,然后再将声音转为文字。这个过程非常艰辛,是一次文学苦旅。其中有一些单篇在杂志上发表过。最近结集成《“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一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好玩的书。
作为汪曾祺研究专家
中华读书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您认为这一获奖作品在您的评论中有何独特性?
王尧:这是我相对成熟的一篇评论文章。我不喜欢孤立地解读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我更愿意将其放置在整个文学史和文学生态中讨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体现在对作家的历史定位上。我以为,在论述一个作家时,批评家需要写出自己的文章。在这两个方面,《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或许相对成熟。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曾祺的散文成就?
王尧:我最初阅读汪曾祺时,未必能理解汪曾祺。读完他的小说和散文之后,我感觉,研究汪曾祺应当将他的小说和散文对读,再综合论述。汪曾祺打通了小说和散文。他的《蒲桥集》出版后,我觉得我在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时应该给汪曾祺专章的待遇。这本书在九十年代初出版,许多观点已经陈旧,但我选择了汪曾祺散文,为这本书留下了亮点。除了语言的成就,当代像汪曾祺这样将自己的人格、性灵、趣味、生活、识见等留在文字中的散文家并不多见。汪曾祺说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并非妄言。
中华读书报:在多次重读中,您对汪曾祺的认识有何变化,今天如何认识他的作品的经典性?
王尧:我现在对汪曾祺的整体评价与2017年写《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时是一致的。汪曾祺是当代少数几位被经典化的作家。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分析他的经典性,他在文化上、修辞上对汉语的修复,是他成为经典作家的主要原因。经典作家在时代之中,又在时代之外。我在纪念汪曾祺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提到:我无法预测以后的文学史会如何论述汪曾祺,但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中,汪曾祺当有一席之地;同样,我也认为,过往汪曾祺研究中的水分或许也会被挤掉。以我的阅读印象,汪曾祺研究中,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从个人偏好出发过度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对汪曾祺“士大夫式”生活方式的过度渲染,有可能将汪曾祺先生的性情与作品变成一种文化消费。如果汪先生健在,他也可能对这些善意的夸大不以为然。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汪曾祺对今天的文坛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王尧:我们可以学习汪曾祺但无法也没有必要模仿汪曾祺。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再造就汪曾祺式的文人。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先生和像他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最后一代“士大夫”。换言之,汪曾祺先生是终结了文学上的一个时代,而不是开启了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对汪曾祺先生的缅怀和肯定,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自己的贫乏有关,与我们创造力的丧失有关。我们需要寻找我们创造文学世界的方式。
作为小说家
中华读书报:2020年,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您曾经提出新“小说革命”的命题。如何理解新“小说革命”?当代小说为什么需要“革命”?
王尧:“小说革命”成了去年到今年的一个话题,《文学报》《江南》杂志组织许多作家批评家回应。如此反响,出乎我的预料。我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中,简明扼要表达了我的思考。我并不否认我们有好的小说,但在整体上,我觉得小说洞察历史、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衰退,小说艺术发展滞缓,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困境,需要激活小说发展的动能。这里的“革命”不是“断裂”,是“延续”中的发展,我们需要探索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那些回应我想法的朋友,让我获益很多。
中华读书报:《民谣》可否视作“小说革命”的实践?
王尧: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民谣》不是用来确证“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的,它是“小说革命”的实践,不是“小说革命”的实绩。我提出的新“小说革命”,不是基于自己的写作,更不会认为自己写了一部异质性的小说就革命了小说。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民谣》的结构?全书分为四卷和杂篇、外篇,是《庄子》对您的创作启示?
王尧:小说的结构其实就是方法论。前四卷在我交稿之前是冠以“内篇”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内篇、外篇、杂篇太整饬了,就删除了“内篇”,想让前四卷敞开一些,内篇、杂篇、外篇的概念是借用了《庄子》。我一直寻思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一是小说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二是作为形式的结构如何成为内容,三是因结构而形成的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我在《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谈到了分裂的语言生活与思想的关系,杂篇和外篇就是呈现分裂的语言生活。《民谣》是第一人称叙述的,这样的视角会有所限制,杂篇相对丰富了前四卷的叙述,在整体上增加了记忆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每篇的注释又带有注释者所处的语境特征。外篇讲述了前四卷中的一个故事,可以呈现由于讲述的年代不同,讲述的内容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结构在我这里不只是形式,也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华读书报:《民谣》的语言绵密雅致。您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样的时间跨度对作品的连贯性有影响吗?
王尧:《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这是我给《扬子江文学评论》写的创作谈的题目。如果说我本人对《民谣》有肯定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民谣》持续写作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我研究文学几十年,知道现当代作家的长处和短处,小说的语言是我的考察重点之一。作家和作家的差异不是讲了什么故事,写了什么人性,说了什么思想,而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讲了故事、写了人性和说了思想。将近二十年的写作,断断续续,每次续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连贯性的问题主要是人物命运的变化和叙述语言的中断。去年春节后,我用了好长时间才进入写作状态,并重写了前面完成的部分。
中华读书报:您做评论多年,对叙述技巧应该很熟悉。首部小说即是长篇,您觉得有难度吗?
王尧:难度主要是我在写作中有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部小说之所以写了二十年,是我一直在寻找我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般意义上的技巧对写作者而言不是问题,当它和调性、思想、故事、情节、细节等融合在一起时,才开始成为问题。这是需要磨合的。
中华读书报:感觉《民谣》自传性极强,这里有您的影子?
王尧:《民谣》当然不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可能是多余的。包括我的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它给读者自传性极强的原因,是叙述的效果。小说里的那个少年王大头有一点我的影子,但他比少年的我敏感、聪慧多了。我少年时看世界的眼光有一部分和这个少年重叠。这部小说的结构和杂篇的注释也有我中年以后思想的影子。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两场大火,一把火烧了外公那边的天宁寺,那里有革命烈士墓和“谁是叛徒”的秘密;另一把火发生在奶奶那边的石板街,奶奶一家的家庭成分和命运因此改变。两场大火有何喻意?
王尧:写作时,我是根据情节的发展写了这两把火。您在问题中其实已经说明了写这两把火的必要。如果说喻意,这两把火成了新旧世界的分野。
中华读书报:读这部作品,我想很多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和您同时代的作家,比如苏童、余华以及格非。您认为讲述自身成长过程以呈现历史的方式,自己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有何特殊性?
王尧:苏童、余华、格非都是我的同辈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研究对象。就写作小说而言,他们是我的前辈。和他们相比,我十分惭愧,他们都写出了经典之作。我现在还不敢和同时代作家比较异同。如果说讲述自身成长过程以呈现历史的方式有什么特殊性,可能是我的文本有多重对话的空间。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样子,您觉得满意吗?
王尧:我不想说我满意的作品是下一部。诚实地说,我目前的能力只能完成到这个程度。就自己预设的目标而言,我觉得基本完成了。在定稿时,我对自己叙事的方式犹豫过,这部小说其实是有故事的,但我把这些故事分散了,读者需要在阅读中去清理和结构。我估计,有些读者肯定不喜欢我这样讲故事的方式。我曾经想做些调整,但放弃了,如果修改了,那就不是我想写的小说了。请读者宽宥我的任性。我在年轻时候就想用多种文体表达我对历史、现实、人性的理解,就此而言,我做到了。有朋友跟我说,写小说会上瘾。好像是这样。《民谣》不是确证我有写小说的才华,而是告诉我: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 王尧:时代与肖像的四重解读[202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