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女工绘》:历史的真实与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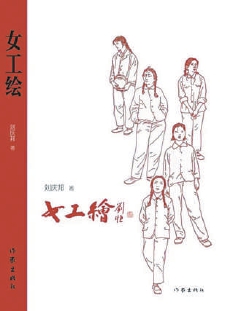
《女工绘》 刘庆邦 著 作家出版社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说:“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当作故事的潜在成分,历史事件则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换言之,当刘庆邦以个人经验来触摸历史的时候,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情境对于《女工绘》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而言当然是重要的,它是小说发生的场域,不同于许多作家对那个年代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肆意解构,刘庆邦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华春堂,还是其他女工们,她们的命运皆是历史现实中的命运,不能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消解对人生苦难的真实认识和人生本质的意义。虽然故事发生在矿区,但是一切的矛盾、纷争与命运的吊诡,无不嵌入那个年代每个人内心的隐秘深处。
《女工绘》让我想起现实主义小说对细节的迷恋,这种迷恋,能够让我们迅速进入小说的历史情境,获得时代背景的某种带入感。或可说,在《女工绘》中,对历史的分析、体认与对人的命运的阐释不过是某种情感的推动力,真正打动我们的是浮动的生活之下的各种细节,不仅是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各种思维与行为方式。虽然小说具有明显的历史色调,但是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一群女工在矿区的生活,她们的爱恨情仇如此诚恳,一举一动,如在眼前。这种诚恳也体现在作家刘庆邦对待生命与记忆的态度上,极力还原历史的现场,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群女工生命本身的尊重,即便小说中那些权力对人性的倾轧、命运的不公与损毁,都在一种极为清晰与理性的记忆中,成为某种见证、清理乃至成全。
这是《女工绘》的丰茂与细腻之处,虽为长篇小说,但是刘庆邦有意摒弃当代文学中惯用的家族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切片般地单刀直入,将人物的活动置于大观园式的“矿区”,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小说都是在狭小的空间内进行演绎、生发,这也是作为“短篇之王”的刘庆邦施展小说技艺的地方,虽然社会空间并不大,但是时代的“红”与煤炭(人性)的“黑”如此鲜明,我们在矿区这个舞台上,看到了时代深深的印痕与女工们心上斑驳的伤痕。从风俗入手,到矿工们因工种的选择而产生命运的变化,从各种隐忍地活着,到爱情(婚姻)的不同抉择,那些被挑选的芳华、被浓缩的事件、被放大的无常,构成了《女工绘》中女性生命的水墨图,矿区折射的乃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矿工的心理图景、人情伦理、道德秩序皆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呈现。
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上,除了对生活的细腻呈现之外,刘庆邦并没有选择男性这一长期以来历史叙事的主角(尤其在男性劳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矿区),而是有意选择了被边缘化的女性作为小说的叙事主角,这使得长期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沉默的女性,发出动人的声音,展露出她们压抑已久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与命运遭际,尽情表现不同于男性的经验以及与男性相抗衡的渴望。
当然,矿区的女人们也是普通人,她们也会斤斤计较甚至勾心斗角,正如当华春堂一心想要去宣传队的时候,她也会对张丽之是否真的愿意帮助她产生怀疑,然而疑神疑鬼、心事重重,是矿区大部分女工沉重心灵的外在表现,只是华春堂在微乎其微的机会里,还保持着作为“人”的精神知觉,虽然这种知觉要时时为“成分论”等思想所左右,但在本质上,她与其他女性一样,无论勾心斗角还是惺惺相惜,都在意图摆脱权力的左右,成为生活情感和日常理智健全之人,唯有这种健全,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
但是,让人感到悲凉之处就在于,她们都必须在权力(包括男权)的缝隙里匍匐前进,忍辱负重。唯有在宣传队的时候,她们的精神世界才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每个女工仿佛从黑暗的矿坑里找到了一丝光亮,焕发出青春本来的颜色,那几乎是一种本能流露出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感。然而,就在此时,小说忽然安插了“傻明”这一角色,这个被人无情戏弄的精神不健全的女子,直接导致了其父的牢狱之灾。我忽然想起本雅明说过的“小说的意义不在教诲,而在向我们描绘某种命运”。刘庆邦借助傻明这个微弱的次要角色,在她一次次被众人侮弄的过程中,也不断唤醒我们对“人”本身的命运的思考。当曲终人散,除了心思缜密如华春堂未雨绸缪,调到了化验室,其余人都成为权力倾轧和阴暗的人性打击之下的受害者。除了工作上饱受难堪,她们还要随时应付工作中的男性骚扰,更多的是要面对因流言蜚语、指指点点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压抑。从《矿上成立了宣传队》到《各奔东西》,刘庆邦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对女工乃至人之存在进行探究,不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更多是通过女性的性别经验的描述,抵达历史与人性的幽微之处。
与其他人物相比,华春堂的个人意志更为强烈,作家有意把她放在女工的中心位置,互相折射,以形成某种参照系,这么做一方面实现对群像的描绘,另一方面也在通过某种具体的青春记忆的描述,唤醒集体的经验以及内心所理解的历史真实,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即便遭遇种种困境与黑暗,也不可遏制的青春力量,正如华春堂周旋于命运的安排,对自身乃至周边的女工的命运与遭际具有清醒的认识,既看惯人世间强加于命运的种种荒唐与错位,又在其中了然自身的优势、劣势乃至人生的底色。譬如从一开始,她就在与其他几位女同学的对比中,获得某种清醒的自信。这是一种争取的姿态,也是一种在时代的漩涡里寻找的姿态:从未否定自己,而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命运中来。
在此意义上,《女工绘》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以特殊年代为背景的成长小说,言其成长,因为小说的后半篇幅,主要笔墨放在几位女工的恋爱上,而此处的“恋爱”有别于从前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虽然男女人物都处于阶级斗争的年代,但是刘庆邦在恋爱问题的处理上,把“恋爱”作为建构人的主体性的主要途径,具有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色彩。譬如从一开始华春堂对魏正方的态度,有故意接近以达到工作调动的目的。但随着宣传队的解散,魏正方悲哀地重新回到掘进队,华春堂依然去看望并鼓励他,表现出一种超越男性的特有的坚强,这是遵循了其内心的善意或者说生活应有的教养。在找对象这个过程中,从李玉清因事故去世,到马成学的刻意接近,再到魏正方重新出现在视野中,直到失败之后遇到卞永韶,华春堂表现出了如调动工作那样特有的自信、聪慧与敏锐,目的明确,心思缜密,虽然几段感情算不上完美的“爱情”,但这里面很少掺杂欲望的成分(或者说,是一种审慎、克制的欲望),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境遇之下,对私人情感归宿的合理诉求,是人向上的冲动,也包含着对自我的发现和不断完善。
爱是一种成长方式,虽然这部小说写到了历史带来的伤害,内部却始终隐藏着某种温暖的力量,那是深沉的爱与同情,诚如刘庆邦在后记中所言:“我写她们,因为爱她们”,每个人都是唯一的,被害者其实也是被爱者,在一种应许的爱与善的包围中,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述,也在真实的层面,实现了对“记忆”应有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