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中国古典文学园地的“楚狂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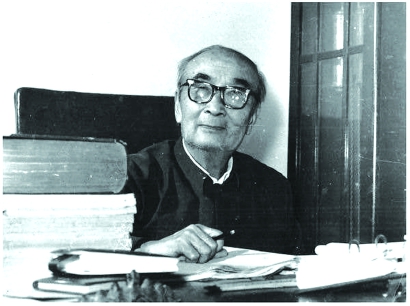
陈子展(1898—1990),文学史家、杂文家。原名炳堃,以字行,湖南长沙人。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结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1932年主编《读书生活》。1933年起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30年代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长期从事《诗经》《楚辞》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初各大学院系调整之后,复旦中文系蓬勃发展,群星璀璨,集结了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张世禄等一批名宿,各自开辟了独立而深入的学术疆域。这其中包括了陈子展先生倾注大量心力的文学史研究和《诗经》《楚辞》研究。
学问之外,陈子展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经济史学家钱剑夫曾言:“展老为人,刚直不阿,畅言无隐。……然人凡有一善,莫不折节下之,揄扬不释于口。常告我:某也贤,某也君子,某之文甚高,人品更高。”这种刚直又包容的个性,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早年享誉文坛的是杂文写作
陈子展原名炳堃,字子展,以字行。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入私塾。三湘地灵人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深刻影响晚清政治的人物皆出于此;近代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进步青年也云集于此。1912年,陈子展14岁,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他迷恋足球,成了校队一员。
当时长沙城里,县立师范和省立师范相距很近,教师在两校兼课,两校学生可谓同门。据陈子展回忆:“当时,我才19岁,和许多同龄青年一样似乎对政治都很感兴趣,常常在校外同行出游,在一起开会议论天下大事,而毛润之又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陈子展《和毛泽东同志同行》)
大革命前夜,毛泽东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湖南青年在长沙办自修大学,校址就在纪念鼎革之际湖广思想家王夫之的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开讲历史唯物论、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课程,学《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培养了一批早期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常于晚间到自修大学讲演。在陈子展回忆里,“毛润之讲得最多的是农民问题,也讲得很深。毛润之在1921年夏秋从上海回湖南后,在搞教育的同时,还在家乡韶山等地发展农民协会。”当时陈子展在师范教书,晚上常被夏明翰约请去一同活动,所以被当成党内同人,有几次还受托去韶山冲给毛泽东送信。彼时他还通过日文阅读河上肇、片山潜等翻译的单篇小册子,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非常重视,也熟悉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论述。这些经历都为他后来牢固的唯物史观打下基础。
1926年以后,湖南办了很多有影响的报纸,毛泽东主笔《湘江评论》,李维汉办《向导》《北斗》,谢觉哉办《湖南民报》。陈子展也在《湖南民报》做过新闻编辑。1927年,大革命形势突变,长沙的国共关系日趋紧张。驻守长沙的国民革命军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陈子展、徐特立、李维汉、谢觉哉等共41人被通缉。陈子展仓然逃离长沙,辗转来到上海,留在长沙的家人也由共产党派人护送来沪,从此一家人定居沪上。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联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陈子展受谢觉哉邀请前往参会并住在他家中。这是他们长沙一别之后,时隔22年的重逢。陈子展曾说,第一次大革命中国共间短暂的合作的突然破裂,使他和毛主席的联系和交往中断了。
1932年,他应友人力邀,开始在复旦中文系教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过,他早年享誉文坛的是杂文写作。陈子展的杂文短小辛辣、辞锋犀利,多以“楚狂” “楚狂老人” “湖南牛” “大牛”等笔名刊行。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曹聚仁等主编的《芒种》等,常能见其小品文。林语堂曾评价,鲁迅以下,有两个年轻人也写得甚好,一个曹聚仁,一个陈子展。黎烈文谈及《自由谈》稿酬是依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而定,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徐志啸《陈子展的杂文写作》)
在文学史领域的先导作用
复旦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于1925年,建系之初,课程设置即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为研究基础。
陈子展写过五种文学史,分别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两种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是陈子展1928年9月应田汉之邀于南国艺术学校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而作。“初拟用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略附鄙见”,后因对“近代”认识主张与胡适不同,自铸新见,成就此书。
历史学家主张“近代”断自1840年鸦片战争,文学史家当时的断代也沿用此种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观念,陈子展则对“近代文学从何说起”作出了新的定义:将近代文学断自1898年的戊戌变法。陈子展认为“古旧的中国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是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的。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既是革新政治家,也是青年诗人。他们鼓吹的诗界革命又是新文学的发端;同时,随着废除八股、思想上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学也因此有了显明的变化。因而陈子展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离开时代便失其生命失其价值。”1898年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年份,如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界一个常识性判断,陈子展的首创之功不可埋没。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被后世的近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为最早以“史”出现的近代文学史专著。其后,陈子展将其扩充、细化并重新设定纲目,于1930年另撰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从宏观上建构框架,《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则广征博引、细致分析,两部著作互为补充。在这两种研究近现代文学的著作中,陈子展不但把近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了1898年,更重要的是,以“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矛盾运动为主线,从“文学发展是自然的趋势”、“外来文学的刺激”、 “翻译文学的介入”、“思想革命的影响”和“国语教育的需要”等方面对文学史进行讨论,把 “最近三十年(1898—1928)” 视作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连续的过程和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来观照,架构起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文学史体系,从而奠定了近代文学的基本框架。陈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刚一问世,旋即获得好评。赵景深先生评价:“这本书是我极爱读的。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毫无生发,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书则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时带诙谐。书中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对文学大势说的非常清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20世纪30年代,陈子展开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真正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教学工作需要,他将学术研究方向定位在了中国古代文学。开始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他写作《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的缘起。据王运熙先生后来回忆:“陈先生很谦逊,建国前夕和我谈到这些著作时,常说这是为了讲课需要,编编讲义,混口饭吃,对其质量不甚满意,这实际也反映出他对学术著作水平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在研究古代文学史的时候,陈子展使用的理论方法,与奠定其文学史研究盛名的两种近代文学史并无二致。第一,始终从白话文学的视域观照唐宋作家创作上的特点,比如专列出敦煌俗文学的发见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宋代平话等章节。第二,娴熟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同类作家作品与相关文学流派分析论证。第三,在征引史料的时候,点出多种不同观点及其材料来源,取精用宏。
《中国文学史讲话》是一部中国文学通史。按照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来编排章节,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陈子展只用了八讲,就清楚地描述了从《诗经》时代到“新文学”运动这三千年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结合他1935年为文学批评课程所撰写的 《中国文学批评讲授资料录要》(油印稿),可以看出陈子展对古代文学史、与文学写作紧密相关的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把握和内在理路。曾跟随陈子展研习《诗经》《楚辞》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在介绍陈子展对《诗经》的研究时谈及,陈子展强调要“绳索贯穿散钱”,屡引明人笔记中的一段话,用绳索和散钱来比喻观点和材料的关系,指出只有用观点的“绳索”将分散的材料贯穿起来,才能成为一种融会贯通的学问。陈子展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上,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试图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相关作品的发表、讲学和传播,无疑在中国早期文学史领域起了某种先导作用,更奠定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领域的学术地位。
毕生学问之结晶的《诗经》《楚辞》研究
陈子展毕生用力最深、成就最巨的,无疑是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他曾在回忆随笔中写道:“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对《诗经》《楚辞》开始发生了兴趣。而两书为当今一般人所难懂。所以,我很想作一番解释工作,以便青年阅读。”
陈子展《诗经》研究的成果,最早的是《诗经语译》,后有1957年的《国风选译》《雅颂选译》。中年之后,治学境界日臻成熟,后期有更深入的成果,包括《诗经直解》《诗三百解题》。研究《诗经》的时间,前后超过50年。
陈子展在探讨《离骚》等议题时,曾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他批评过郭沫若和高亨在研究《诗经》时过分相信和使用假借,从而常得出不够客观的结论。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认为“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陈允吉曾注意到,陈子展先生研究《诗经》,论及《北门》《定之方中》《黍离》《兔爰》《楚茨》《生民》等篇,都汲取了郭沫若的成果。陈子展说过:“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他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看法,绝不人云亦云。
王运熙留在复旦中文系任教之初,做过陈子展助手。王运熙曾谈及,当时大家学习《诗经》,用的是余冠英的《诗经选》,但他认为陈子展的 《国风选译》《雅颂选译》学术性更强。殷孟伦所写的《诗经》研究论著提要,对陈子展的成果作了较高的评价。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杨晋龙也认为,陈子展可作为“民国以来研究《诗经》的代表”。而陈允吉认为还可补充一句:“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当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刊出以来最重要的《诗经》研究成果。”
陈子展的《楚辞》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他翻遍了历代注本,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西方理论家的论著,参考了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他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独立思考,一一予以爬梳澄清。不仅如此,陈子展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的高度,认为屈原的作品堪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陈允吉《刚留校时,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诗经〉》)
陈子展利用业余时间查询逾千种资料,经过二十年整理,尤其在苍黄时节之后,仍以八十高龄醉心于《诗经》《楚辞》研究,最终完成了他自称为“一生所在,唯此两书”的《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他之所以会花费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于这两部《直解》,是因为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投身其间,几易其稿,荟萃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向学界和世人奉献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在《诗经》《楚辞》研究外,陈子展还有一些自己颇为重视的专题论文:比如《孝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所生之影响》《秦汉隋唐间之百戏》,前者据说金兆蕃读后十分赏识,金老是清末民初诗文大家,他向时为复旦教务长的次子金通尹推荐,金通尹读后也大为嗟赏,遂力荐陈子展从兼职教授成为复旦专职教授;比如《八代的文字游戏》,抗战结束以后,复旦所谓的京派四教授:梁宗岱、方豪、蒋天枢、邓广铭(邓当时是副教授),说陈子展是海派领袖,要掂他的份量,请他为他们所办的刊物写文章,陈子展奋笔疾书,一个星期就交出了文稿。陈允吉回忆,陈子展倒并不自认为是海派领袖,他说自己是不京不海不江湖。其实湘学传统和楚文化,对陈子展的影响非常深刻,王先谦、王闿运、杨树达等湖南前辈学者,都是他一生崇敬的对象,而他自己的文章,也大多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陈允吉《刚留校时,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诗经〉》、陈左高《江山代有才人出》)
文学也能改造人们的落后面貌
陈子展青年时期的理想,就是“做个韩愈《师说》篇里所说的传道受业解惑者”。当时,他目睹国家的落后,科学的落后,认为这种落后局面终究是和人的落后有关,而人的落后就是教育的落后。因此,他认为教育工作或许是救国之道。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他在长沙教书,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希冀将个体的力量汇入到唤醒国人、振兴祖国的时代洪流中。
陈子展后来在大学里教的是文学,他认为:文学也能改造人们的落后面貌,鲁迅即因此弃医从文,因而我亦以文学事业为理想,用之奋斗,孜孜不倦。(陈子展《以人民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
陈子展执教复旦,有两件事特别能反映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和奖掖识拔后进的惜才之心。一是杨廷福在抗战初报考复旦中文系,英语和语文俱佳,数学考了零分。陈子展排除当时国立大学要看总分的规定,再三争取,学校才破格录取了他。杨廷福后来成为了中国法制史学家,对玄奘也特别有研究,相关成果还曾得到季羡林先生的推荐。另一位是鲁实先,陈子展引荐他当教授时,他才二十出头。当时有人不满,称他为“娃娃教授”。陈子展的理由是,鲁实先在文学、考古学上都很有造诣。鲁实先当时写了《殷历谱纠譑》和《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指出了董作宾《殷历谱》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的许多错误,引起很大的反响。陈子展为他撰写了《龟历歌》长诗和《题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七言绝句六首,批评了傅斯年、董作宾等京派教授。鲁实先的这两项成果和陈子展为他题写的诗,后来得到郭沫若、杨树达、顾颉刚、胡厚宣等的好评。
陈子展那一辈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大都受过五四思想的洗礼,追求为学的专精,也崇尚学术自由,鼓励青年有独立的见解,虽重视学问的传承,但并不刻意讲究局限于门户的衣钵相传。
上世纪60年代,陈允吉留校成为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后,曾根据系里学问传承的安排,跟随陈子展学习《诗经》《楚辞》,对其为学授业的风格印象深刻。
陈子展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他强调要多读基本古籍。中国古典文献的要籍是核心部分,要尽可能多读,俾在知识结构中形成一生受用的“压舱石”般的基础,便于融合其他知识,而不是具体需要研究什么问题时,才临时去读这些书。
比如,他提倡“精读与翻阅相结合”。读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每一部都读得很细。他经常引用《魏略》记载诸葛亮读书“独观其大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谓其“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故事,来说明精读与翻阅要结合起来。
比如,他强调要“博观约取”。观察接触的东西务求其博,而研究的题目必须约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以内。博观是手段,约取是目的,博观是奠基,约取是在基础上进行建筑,博观是增加感性认识,约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他自己的研究也贯彻了这一点,为研究《诗经》作了长期积累,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学、古代社会研究、文物考古(他特地订阅《文物》杂志随时参考)、生物学等等,都有涉猎。
《诗经》学习过程中,陈子展请陈允吉自己选不同的本子对照阅读,他非常开明,认可青年自主的探索。《诗经》《楚辞》是陈子展和蒋天枢教授共同的研究方向。陈允吉特别强调:《诗经》传播史上有三家诗与毛诗之争,陈子展先生倾向三家,而蒋先生独主毛传,尽管门径不同,而他本人的观点也延续了陈子展的观点,但蒋先生对他也予以肯定,可见老先生们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服膺真理。——只有这样的治学环境,才能奠定复旦中文学科的深厚基础和淳正学风,达到学术上的领先水平,也才能孕育出人文学科的大师。
陈允吉系统地跟随陈子展学习《诗经》不到一年时间,对于这段时光,他非常留恋,也从读书过程中体会到这是很好的培养方法。
陈子展先生晚年,大多数时间在家闭门做学问,这令他在复旦园里颇有一些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尽管极少带学生,但对于“传道受业解惑”这项青年时期就立志的事业,他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谨严和坦诚。
陈子展三十年代曾在《申报·自由谈》上作诗:“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辱,日长聊以消忧”。这是他作为读书人的朴素理想,也可视为其一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