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加·凯雷特:不研读人类的弱点,我们将永远不会了解自己

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以色列作家身上,多有一种贯穿时间乃至超越时间本身的纵深感。但在埃特加·凯雷特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痕迹。他总是轻盈地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开凿出如同爱丽丝梦游过的那个奇境,奇境里有完全不同于我们世界的生活准则,却又完美接续着已存在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温凉妥帖地契合人心,让所有走进他的故事的人都在叙事的小宇宙里深深迷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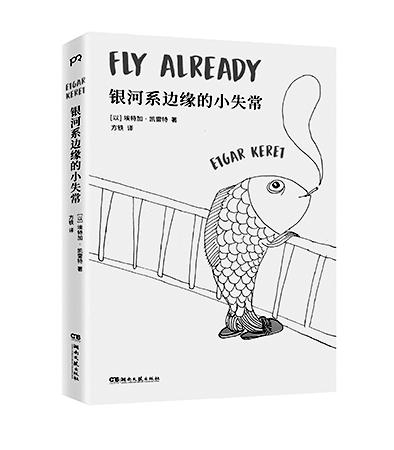
据说在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是作品失窃次数最多的作家。虽然这一点很难在统计学上精确展示,但他的确曾经收到来自书店的信件,请求他选择在夏季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夏天人们穿得单薄,不太容易在衣服里夹藏书本。他是许多年轻一代以色列人心中的文学偶像,也是当下是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被译为42种语言。他笔下已有50多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数次获得以色列出版协会白金奖,并获颁以色列地位崇高的总理奖、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法国艺术暨文学骑士勋章、英国《犹太季刊》小说奖、全美犹太人图书奖等。
阿摩斯·奥兹、大卫·格罗斯曼……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以色列作家身上,多有一种贯穿时间乃至超越时间本身的纵深感,来自于悠远历史的宏大魅力与数千年来这一民族饱经沧桑一路走来的艰辛,在他们的作品中拥有深刻而清晰的印痕。但在凯雷特的作品中,你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痕迹。他总是轻盈地讲故事。或者说,他善于把许多我们认为格外沉重的题材,改造成人们能够轻而易举被打动和接受的方式。在他的写作中,短篇小说无疑占据了绝对比例,将创意无限的故事情节浓缩在也许只有短短数页的篇幅之内是他的标志性创作,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几乎不在他的考虑范畴。有读者说,凯雷特是一位脑洞大开的作家。其实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当你将一个在内容幅度上极其丰富的故事浓缩到如此精炼的篇幅时,任何描述方式都会显得格外戏剧化。
身为作家、同时也是编剧的凯雷特非常清晰地知道在故事的何种关节上施加力量,便能让一个似乎老套的故事焕发出全新的魅力。他更擅长的,是在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开凿出如同爱丽丝梦游过的那个奇境,奇境里有完全不同于我们世界的生活准则,却又完美接续着已存在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温凉妥帖地契合人心,让所有走进他的故事的人都在叙事的小宇宙里深深迷醉。
不久前,他的经典之作《想成为神的巴士司机》和最新作品集《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由浦睿文化推出中文版。记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谈及以色列作家,许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是阿摩斯·奥兹、大卫·格罗斯曼等站在历史层面书写的作家,但无疑,你的作品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除了独特风格之外,你是否认为这其中也有时代的原因?在你的感受中,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样式是否已经发生改变?
凯雷特:由于以色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我觉得我以前的几代作家都写过小说,来试图描述和讲述以色列人民作为一个群体的故事。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我的成长时期,这个国家已经对其身份有了更为确定的定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写一些更私人和个人化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写一些较少涉及该地区,更多关涉个人和人类普遍状况,而可能并非投射于国家际遇的故事。
记者:故事是永远在变的,但人的困惑和脆弱却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不断遇见的情绪,是否因为这个,才使得你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写作?
凯雷特: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到生而为人的脆弱性和存在主义的混乱,他就没法真正理解人类的状况。当我们讲述我们的故事时,经常倾向于试图隐藏自己的困惑,只谈论那些代表着力量的品质,如勇气、毅力等。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是最强壮和最聪明的人,他的人生仍然会有脆弱和困惑的地方。如果不去承认、不去研读这些人类的弱点,我们将永远不会真正了解自己。
记者:你曾提及自己受卡夫卡的影响,与写作中的荒诞感和超现实主义相比,其实你和他更相近的是在强烈戏剧冲突中保持着人性关怀,流露出同情、善意等,这似乎不是可以“学习”而来,更像是天生的。不知你如何看?
凯雷特:以卡夫卡作为我的文学偶像,在我看来是因为他愿意与他的读者分享他最大的弱点和焦虑。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人类的诸多弱点来认识到“人”这回事究竟是什么。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中有许多希伯来俚语,有古语传承的中国人一贯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力量。在你看来,希伯来语的力量和魅力是什么?
凯雷特:希伯来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法使用这种语言,但在这段时间里,希伯来语一直作为圣经的神圣语言保留在集体的知识里。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才开始重拾这种语言。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这种语言中缺少了人类历史在2000年时间的发展中产生的事物,比如冰箱、香烟、水龙头等等,所有这些在古代都不存在,因此,在希伯来语中也不存在。因为人们在讲述中不时会需要这些词,所以希伯来语在俚语和文字创新方面有很突出的表现。当然,希伯来语的俚语,就像任何俚语一样,可能是非常混乱和颠覆性的,而这种语言本身是非常古老、神圣和保守的,标准语言与其俚语之间的张力在语言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紧张,这也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新国家在很多方面紧张关系的一种反应。所以我必须说,希伯来语是一种很棒的书写语言。
记者:在你的写作生涯中,是否曾有某些瞬间,会觉得有些故事没法在一个短篇的篇幅里言尽?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时,你是如何做的?
凯雷特:这情况几乎时时发生。即使我写了一个自认为很棒的故事,我仍然觉得,我能在写作中所描述的,其实只是自己正在经历的情感漩涡的一个片段。
记者:之前据说你开设了一门创意写作课程,这门课程如今还在继续吗?
凯雷特:我是BGU(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的教授,我在那里举办写作工作坊。其实我并不自信能教会这些学生怎么写作,但我确实觉得,通过提供给他们适当的问题和一些挑战,我可以让他们在我们的写作工作坊中发现他们各自充满诗意的写作世界。
记者:关于创意写作课,你曾说这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地方,让许多人看起来奇怪的写作愿望被视为重要的和合法的,并且成为一个空间,为我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文章提供完美的音响效果。所以你也许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写作不应该是孤独的一项工作,而是需要被鼓励和获得认同的。
凯雷特:我认为独处或者同伴都是创作过程中所必需的。对于写作的人来说,一个故事本质上就是一种你想要与别人分享的内在感受或者内心浮现的画面。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至关重要:你需要呈现你的内心世界,而且是不改变它以迎合公众的口味;同时,你想要分享的所有这些图像和感觉是能够被你的读者理解和感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独自写作,但也要与你的编辑和所信赖的读者沟通、交流,并在这种具有批判性的对话交流中找到自己那个适当的调性。让你的作品和内在世界容易被理解和被接受,与此同时不损害它的独特性——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艺术家的终极任务。
记者:擅长写短篇小说的雷蒙德·卡佛曾提到,在他的书桌前(或者说是在他的脑海),有很多时刻提醒他应该如何保持写作心态的便条。对你而言,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这样的便条存在?
凯雷特: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写作习惯。对我来说,我最终会动笔写下的那个故事,一定是因为某个形象或者某种感觉就像在追捕我一样萦绕不去,逼迫着我将它分享出来。在那一刻出现的时候,即使身在中央车站,我都能像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样奋笔把它写下来。或者就像钓鱼那样:一旦你钓到一条鱼,这时候你是在海里钓鱼,还是坐在自家厕所里钓鱼都无关紧要——鱼已经上钩了,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坚持下去,把它钓上来。
记者:在中国,有不少你的作品在宣传时会这样介绍: “作品曲折动人,结局出人意料。”你是否认同于这样的介绍?在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中,我觉得“出人意料”应该并不是你的写作意图,而只是在凸显主题时恰好选择了这样的叙述方式?
凯雷特:在写的时候,我并不会设立一个“要让读者感到惊讶”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和他们分享我的生活经验,因为我把生活看作是一种奇怪的、感人的和完全不可预测的东西,所以也许这些部分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惊喜。每当读者感到惊讶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其实是我每天在床上醒来时,发现周围有一个令人惊奇和疯狂的世界时,我的感觉是什么。
记者:关于你最新的作品《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一些评论提及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和以往的不同之处,对于家庭关系、血缘关系的理解和阐述也多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凯雷特:《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是一个非常折衷的集合。这里面既有类科幻故事,也有寓言,以及特别现实主义的故事。在这个作品集里,我所尝试的是制造一个不稳定的世界,让读者体验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似乎自己所站立着的土地正在不断地被拉扯、改变。这正是生活在一个技术、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不断以疯狂的速度变化的世界里时我自身的感受。我试图通过改变故事的风格、体裁,有时甚至改造故事所在的宇宙,与读者分享这种感觉。
记者:《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这一个短篇本身关乎一系列信件,我发现其中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不仅仅是关于人性,也有对于历史和当下的一些看法。比如在通信中,你会发现一类人的存在——其实现在真的有许多人绑架历史而为自己的当下需要服务,这种趋势这几年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这个小说,你想说的是什么?
凯雷特:我认为,这个故事主要是关于犹太人无意识地分享了一种集体受害者感觉,这种感觉,以及出于对历史重演的恐惧,使我们这些身为受害人的犹太人有时反而会激起别人被冒犯和不耐烦之感。
记者:这个新的故事集中,不少篇目讲了中年人的生活,在中国有句俗话,“上有老下有小”,指的就是身处各种义务中、很难逃脱或者为自己而活的中年群体。而且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断出现。对于这一群体,你有何建议?
凯雷特:只要存在于世,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兴奋和难以忍受的部分。做孩子,做少年,做青年都不容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期,其实都不断面临着挑战和挫折。中年时期可能尤其困难,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一切似乎在朝上走,而当人到中年,你的野心和精力慢慢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大。当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成功的样子时,有些人会因此大受打击,感觉他们已经输掉了关于人生的这场竞赛。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故事里,我想写的是,即使疲惫不堪、日复一日的中年生活,也随时可能有某种东西突然觉醒,把你的生活重新点亮。
记者:在你心中,一个理想的读者会是什么样的?
凯雷特:一个好奇、无畏和灵敏的,足够跟得上我的故事想给他(她)带来的任何冒险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