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三代师生读城记
来源:北京青年报 | 袁一丹 等 2020年08月12日07:16
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新近在三联书店出版《想象都市》与《记忆北京》,以“想象”与“记忆”的角度阐释北京城的文化底蕴。袁一丹为陈平原教授的博士生,在她执教的首师大文学院,她带领本科生重走京城的人文线路,三代师生共同进行了“读城”活动。
——编者按

陈平原(前排右三)、夏晓虹(前排右四) 带学生游永定门

本文作者袁一丹(中)与本科生游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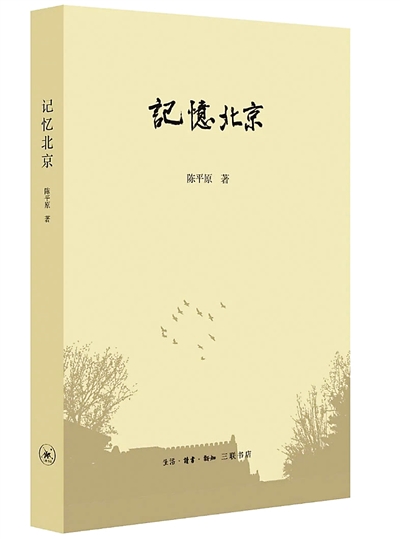
《记忆北京》,陈平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3月出版
理想的都市研究者,不总埋首于故纸堆中。他乔装成走街串巷的负贩,黄昏时分敲着小铜锣,踱入某条胡同。挑子上挤满各色玩意儿:糖瓜、陞官图、兔儿爷、霸王鞭、沙燕风筝。春夏之交,则改作卖花生意,吆喝着:“玉兰花儿来!茉莉花儿来!玉簪棒儿来!香蓉花儿来!叫知了儿!”伪装为负贩的都市研究者,用七个须、八个瓣儿的晚香玉或一尊兔儿爷,推开胡同人家的院门,换取在地者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样式。
“接地气”的都市研究,始于“盲目”的行走,而非居高临下的俯瞰。若把都市看作一个被反复书写的文本,负贩式的穿行是对这个文本主动且精微的语法考察。
专业化的都市研究,固然离不开坚实的文献基础,研究者仍不妨从自己最熟悉的局部出发,打破玻璃隔板,诉诸直接的见闻感受。都市研究在追求历史感与阐释力的同时,还应略带烟火气,贴近平凡人生卑微哀乐,传递出在地者饱满的生活经验。比文献爬梳、理论提升更难的是,学会用在地者的眼睛打量周遭、用在地者的语言记录细节。
将《想象都市》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对读,方能理解陈平原都市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论述姿态。在《记忆北京》“小引”中,作者坦言自家都市研究“不够纯粹”的一面,即书斋之外的现实关怀。面对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人文学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吁,渗透到陈平原的都市研究中。这些无法摒除的杂念,依违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目光,或正是扎根本土的都市研究不同于海外城市研究的出发点。
介于专业与“爱美的”(amateur)之间的田野考察,是让学院派的都市研究“接地气”的一条小径。陈平原更看重都市里“爱美的”田野考察——“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脚步,用你的学识,用你的趣味,体会这座城市”(《“五方杂处”说北京》)。他在北大开设的都市研究课程,意在引导学生亲手触摸北京这座古都的脉搏,进而将这种兴之所至的触摸转化为专题研究。我对抗战时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兴趣,即发端于此种“爱美的”田野考察。
打开《记忆北京》,最令我感到亲切的是《宣南一日游》这篇小文。文中提及“请正研究沦陷时期北平的博士生袁君整理相关资料,印成小册子,加上十几张各时期的宣南地图,让每位参加者心中有数”。这册自制的宣南游览指南,我至今仍保留着,作为自己在陈师指引下步入北京都市研究的纪念。由此养成带着老地图游北京的习惯。
日后读到周作人翻译的永井荷风的文章,更能领会陈老师的用心。著有《东京散策记》的永井荷风,习惯将蝙蝠伞当手杖,拖着木屐,怀揣江户地图四处游荡。走在现代的街道上,对照古时的地图,将江户之昔与东京之今相比较,不免有如读法国大革命之感。在永井荷风看来,精密正确的东京地图,“失却当意即妙的自由”,难以引发游客的兴味。反倒是“不正确”的江户地图给人更多联想空间:在上野点染几朵樱花,在柳原添上一团柳絮,在云边描画一抹淡淡的山痕。这种“写意派”的制图方式,使现代读者能由当下的地名悬想昔日的风景。这或许是当年平原师命我搜集宣南历史地图供同门参考的用意。
2013年起我在首师大为本科生开设“现代文学中的北京”,仿效平原师的做法,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开展“爱美的”田野考察。曾以寻访“千秋翰墨林”为主题,策划琉璃厂一日游。当时设计的路线,以正阳门为起点,经前门大街,折入大栅栏,穿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游琉璃厂一带,再走南柳巷、椿树胡同,出虎坊桥。这条考察路线串联起与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几个亮点,如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青云阁,前者是沈从文北上最初落脚处,后者是鲁迅等人常去的酒楼;又如南柳巷40号晋江会馆系《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故居。琉璃厂周边当然是此行的重头戏,我带学生参观荣宝斋、汲古阁、火神庙,一路讲旧书肆的诗意空气,清季京官“冷摊负手对残书”的风度,郑振铎寻访北平笺谱的经过。在逼仄残破的酉西会馆,听选课同学报告“北漂青年”沈从文如何对琉璃厂这所明清两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馆倾心神往,为他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物研究埋下伏笔。
“想象”与“记忆”是陈平原都市研究的两个关键词。想象都市的媒介,不止文字,他更强调图像与声音的妙用。关于图像北京,可参看《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的相关论文。更有挑战性的课题是利用文字与图像,复原北京的声音风景。我曾在课上问学生,如要为北京建一座声音博物馆,你觉得什么声音能代表这个城市?有人用刘心武的小说来谈钟鼓楼,有人引竹枝词中“冰盏丁冬响满街,玫瑰香露浸酸梅”,有人从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中发现磨刀剪的“惊闺”,有人在《北京风俗图谱》中搜寻各种叫卖声,还有人翻出陈师曾笔下“夕阳院落听宫徵”的话匣子。除了这些已经消逝的声音风景,能代表北京的还有晴空中悠远的鸽哨声,入夏后草丛里的蟋蟀声……去年一位同学的课程作业,出乎我的意料,他注意到北京站“东方红”的报时声。他陈述选题缘由时说:
北京站是一个纷杂之地,“三教九流”这里都有,偷偷倒票的黄牛、附近小宾馆的揽客者、黑车司机,隐秘地在此生存。它也汇集了很多情感,每天多少幕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在此上演,这里有最鲜活的人世。北京站是一条分界线、一圈结界、一个“中转站”。尽管北京站是很多人的终点站,但是这里是作为很多人背井离乡踏入北京这个新地界的中转站。这里有对未来热切的期望,奔生活的真实。
因此我想探索关于北京站“敲钟人”与北京站,与“东方红”之间的故事以及客居者、北京人和北京站曾经的牵连,“东方红”这个旋律在他们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样的痕迹。
这段选题陈述让我想起陈平原在回答“为什么是北京”时谈到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初春破晓时步出火车站,闻到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是凛冽的北风、家家户户煤炭的呼吸、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再加上汽车尾气搅拌而成的气味,这就是北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北京记忆。都市研究的意义,除学术上的推陈出新,理应包括代际间的记忆传承。在这方面,学生给我的启迪与感动,比我在课堂教给他们的东西多得多。对90后、00后而言,接触都市研究与其说是为了掌握一套高大上的理论话语,不如说是个体的回溯与探寻。他们从个人成长史中提取的记忆符号,往往能打破我对北京的刻板印象。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筒子楼、学而思也是北京。豆汁、灌肠、卤煮是北京,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未尝不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一位辅修生,将北京公交系统比作“任督二脉”,按运行路线分为外向型与内向型,留意到这两种性格的公交路线,冬天车窗上创作风格的不同。还有一位学生提交的作业是“城市的裂缝”,关注那些三不管地带的街头露宿者。这些敏锐细腻的观察,已走出怀旧的情绪,触及城市发展的代价,进而有为“失语者”发声的意愿。从平原师处学到的视野、方法,从学生身上看到的好奇心、正义感,都成为我在都市研究上继续前行的动力。
寻访老北京——
“爱美的”田野考察侧记
寻访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指导教师:袁一丹
南柳巷与童年记忆
文/闫思雨 闫巍
南柳巷是我们组成员都很喜爱的女作家林海音的故居,偶然在电视上看见关于林海音故居的报道,一下子就想起了孩提时期读的《城南旧事》,所有记忆纷涌而至,无比怀念。怀念回不去的童年时光,怀念小时候的一切。
林海音生于日本,后随父母返回台湾,后迁居北京,在北京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光,并写下了《城南旧事》这本脍炙人口的童年追忆录,引起无数共鸣。我们本身就是出生在小胡同的北京土著,虽然随着时代发展北京城的变化已经很大了,但仍能跟着《城南旧事》回到童年,所以也想去《城南旧事》的摇篮南柳巷,去重温《城南旧事》和我们一去不复返却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后一片净土的童年。
法源寺尽兴归
文/陈凯迪
四月维夏,犹有暮春之感,访真觉寺,四顾寂寥,石像静穆,颇有访古探幽之趣。灵光乍现,遥想宣南法源寺,唐代古庙而绝少人问津。人道是,戊戌梁、谭二人尝访。千禧年间,因琉球李敖同名小说,坊间讹其提名诺奖,暴得大名。甲午年又得燕都田氏沁鑫,改编为话剧。一时传为佳话,法源寺门庭若市,访客络绎不绝。是岁维新两甲子,遂定北京法源寺为题以作之。
从宣武门外行百二十步,至西砖胡同,遂见琉璃瓦下法源寺。步至前庭,丁香芬芳而争艳,佳木葱茏而可悦。午阴嘉树清圆,鸟鸣嘤嘤,蝉声吱吱。亦有一猫闲步林荫之下,清风徐来,日影摇缀。入大雄宝殿,宏丽庄严,香烟缭绕,有乾隆手书御匾,曰“法海真源”。佛像慈悲,二三僧人诵经不止,四五信徒叩身祈祷。已而叹曰:鸢飞戾天,望峰而忧心难息;经纶世务,窥谷而醉不知返。人之一世,繁华靡丽,过眼皆空。执念何凭终了了,机心虚妄具空空。岂求佛法于外乎?
日光西落,暮色苍然,尽兴而归。至东二宿舍,所辑材料,剪编俱一人作之,欣然忘食。疏星映户,月悬中天,始觉饥肠辘辘耳。然视频乃细水长流之事,非可毕其功于一役。月色入户,辗转反侧,寤寐思之。匆匆二十余日,乃成。今余将离京返穗,忆往昔犹历历在目,故为之文以志。
天桥的那一片回忆
文/陆萍 马瑞 魏学通
北京天桥,应当有两个含义:一是那座供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本身;二是因天桥而得名的一片极具特色、汇聚三教九流的区域。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桥本身不复存在,只保留了天桥这个地名。而随着时代变迁,天桥区域没有了民国时的盛况,但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于是,我们打算探求新老北京天桥各具特色的记忆。
天桥是小时候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提起“天桥”会想到天桥的杂耍,对“天桥”的记忆是虎坊桥永远排长队的炸糕,小时候经常去的友谊医院。还有输液一宿结束后,第二天到友谊医院对面小胡同的小吃店,护国寺的驴打滚,搬迁后的卤煮店。还有记忆中的天坛公园,每次都有很多爷爷奶奶在里面锻炼身体,抖空竹,甩鞭子,小时候合影过的祈年殿。
记忆中的“天桥”好像一个点,由这个点可以拓展出那一片的回忆。
老北京挂历摊儿
文/赵妍 余甦 王瑶
我们这么大的人,大都经历过给教科书包白书皮的年代。在我们的记忆里,一二年级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用挂历给书包书皮。硬硬的挂历包出来的书皮平平整整,非常舒服,这是我们小时候对挂历的印象。而不知道什么时候挂历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淡出了。而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很多老物件都已经淡出了生活,突然回想起来,心里觉得有些不舍。
挂历记录着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有着时代的特色,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即使如今它已淡出人们生活,但还会有人对它视若珍宝。我们在课下遇到了一个挂历摊,“可能是北京城的最后一个挂历摊”。我们想从挂历入手,记录在生活中淡出的老物件,也记录一段儿时的回忆。
毛猴儿的雍容
文/黄兰岚
其实哪里有什么不解之缘?多半是有心人和有意人。有心人去做毛猴了,把技艺传承下来,有意人把毛猴摆在博物馆里、铺进邮票里,供我这样无意的闲氓,去发现其间那点子趣。
毛猴这小玩意儿,选用蝉蜕辛夷这样一些东西来做,组合起来的确会让一些心善的女孩子吃惊。我把这东西介绍给别人,就两次见到第一次认识它的女孩子说,这是拿真的虫子做的吗?当然,知道实情之后这样的担心就作笑谈。
的确,毛猴属于北京,我作为外地人心甘情愿承认这一点。我们去找一位做毛猴的手艺人孙怀忠老师取材时,听说武汉也有毛猴。“但是”,上了年纪的孙老师说,“他们做不出来好的,没见过真毛猴。”说话的神情挺微妙,是手艺人对同行的惋惜与嘲弄。这似乎也是在申明,京味儿是不能攀附电子光纤的,无论历史怎样更迭无方,它永远在地,永远缭绕在阜成门到朝阳门、安定门到永定门之间。
其实孙老师是河南人,据他说,他的老师叶贤良先生是毛猴手艺人几代的传人,似乎是在民国时期举家搬迁到河南居住,毛猴技艺就这样跟去了河南,他跟叶先生学了手艺之后又带着毛猴重返北京,过了一段时间的北漂生活。好像北京真有磁力:它塑造了人,借人之手创造了它的肌理,这肌理不甚缜密却绝不多余,即使被携往他乡却终像小磁石一样飞回,啪嗒一声清脆地归位。
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完全城市化的人,与乡土中国断代的一代人的典型。第一次看到毛猴这种“土味”艺术品时,我感到的完全是新鲜。事实上,我想,这样的玩意儿对于北京人来说,即使是第一次见大概也是会感到亲切的。
在历史上,毛猴也曾是风靡京城的玩意儿之一。“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毛猴,小孩子都会。”孙老师说,那时候清政府过度的重农抑商政策养出了大批富贵闲人,旗人为最多,“都用赋税养着呢。这些旗人贵族不比金,不比银,就比这‘玩意儿’(做由袖筒掏东西摆在手心状)。”
毛猴传到宫里,深得慈禧欢心,“为什么呢?因为慈禧小名叫玉兰,毛猴身子什么做的?玉兰骨朵儿。”这样一说,倒是给毛猴添了一点奇异的美。其实毛猴乍看毛毛糙糙,仔细琢磨起来却发现它的头和四肢恒定地反射着油滑的辉晕,腿部自然弯曲,身上绒毛微微发白,疏密有致。精致如此,反倒把丑的感官印象消解了。搭配上那些袖珍的饰品配件,做出一个有排场的情境,再在底下加一个漆木底,罩上一个玻璃罩,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小剧场摆在大雅之堂上的画面。或说,清廷覆灭之后,一些落魄旗人仍以做毛猴自宽,听来总能引起一些悲凉的微笑。
想来,在民间野地,毛猴常被平民做出一些讽刺达官贵人的丑态,很带有些反抗的激愤的力量,但是在其他的大部分题材中,毛猴的制作与观赏还是蕴藏着老北京人——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都有的那种对人间享乐的痴迷,这种享乐感可以是平常的,可以是雍容的,但雍容因为其起源的民间性,最终也还是平常的。
北京学生的课外据点
文/阚萧阳 孔怡然 卢宇诺
一代人有一代人童年时玩耍的据点和方式。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我们父辈一代人,他们的童年据点可能是大院、胡同、单位家属楼下的空地,在“据点”里吃5分钱的奶油冰棍,喝北冰洋汽水,玩“踢罐颠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据点与玩法已经和父辈的北京人迥异。对于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学生来说,学而思是一个他们不可能没去过的地方:在这个神奇的遍布京城每一个角落的补课机构里,你不仅能学到知识,还是一个能和你本以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朋友重逢的场所。在学而思,遇到你的幼儿园同学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中学时代的课外补习机构,是朝花夕拾的地方,是发展感情的地方,是夹在疯狂学习与彻底放松中间的另一种青春狂欢方式。楼道间打一个招呼,中午一起去楼下买一顿即食午饭,分班测试后一个只能意会的眼神,都是确认彼此身份的方式。
高考对很多北京学生来说,又是一次地理上的大分流。高校语境下的过往身份确认,已不能再通过学而思等课外机构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地方,而渐渐变为各大商圈中的餐饮商铺:化着元气少女妆的几个正在吃烤串的女青年,却在谈论高三晚自习的故事;已经被搬砖和过柱子折磨得快秃了头的几个大小伙子,在一家快餐店里又像高中放学时那样约起了打球的时间。中关村食宝街,毗邻北京高校的数量在京城名列前茅,自然会成为许多北京学生“约”的最佳场所。更为刺激的是,第一次去食宝街见旧同学路上的你,可能就看到了高中同学和他的新女朋友手挽手走在一起;在发完分米鸡求赞的朋友圈后,离你几桌远的另一帮正在聚会的旧友给你点了赞。
中学时代在学而思挥霍好时光,大学时代则在食宝街一边挥霍,一边追忆。无论据点是哪,一起上课也好,一起吃分米鸡也好,这一群曾经以理想主义至上的学生都在反复地确认着自己的身份,积极地践行着村上春树那一句“至死都是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