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故事集》:杂语、对话与心灵的复活
来源:文学报 | 徐兆正 2020年03月01日0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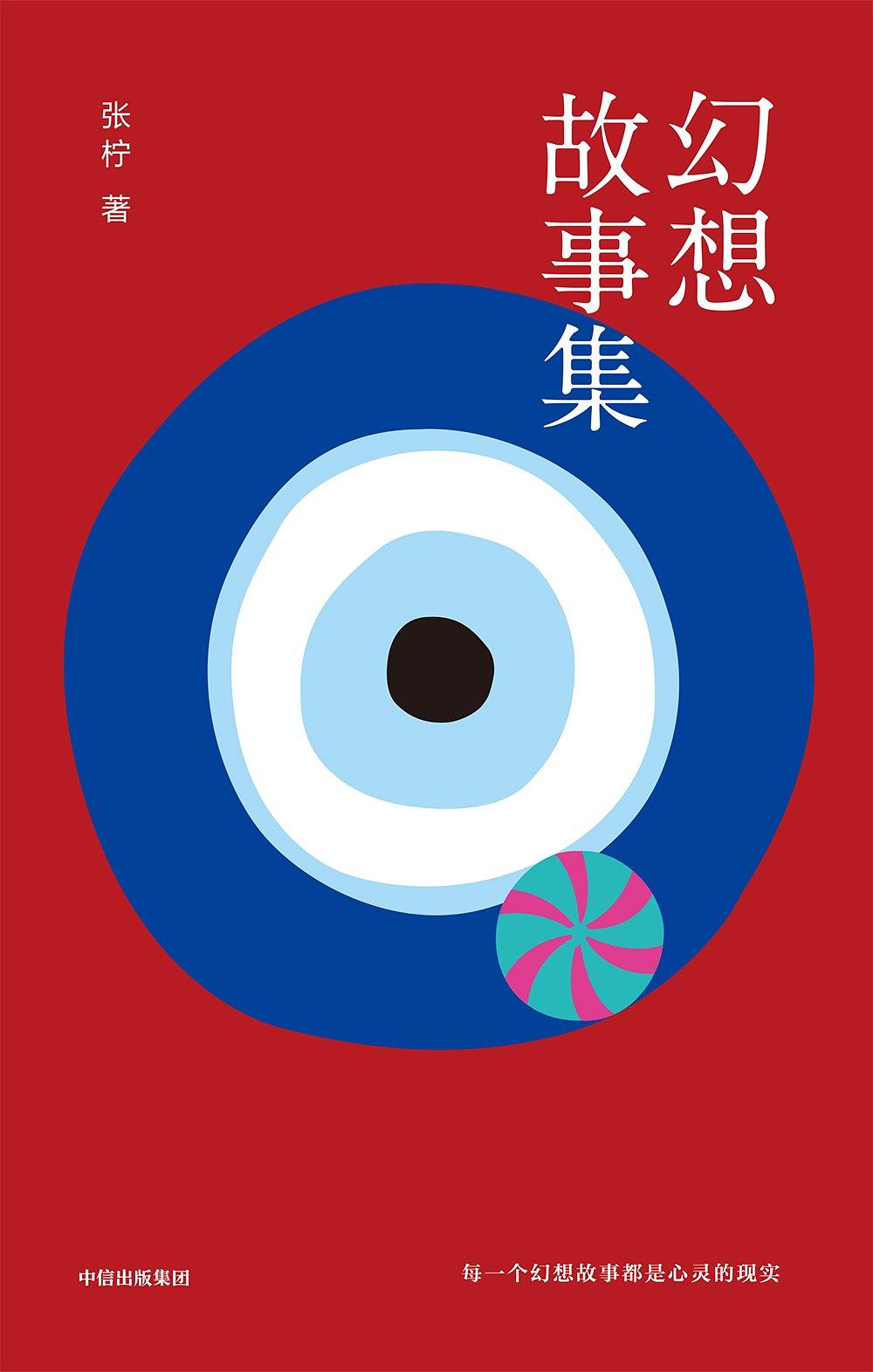
《幻想故事集:八个城市梦幻》
从《罗镇轶事:六个乡下故事》的杂语,到《幻想故事集:八个城市梦幻》的失语,最后到《旷野集:三个女性故事》中的对话,我们一步步地看到那些已经成为 “失语”的“杂语”是如何重新舒展成为“对话”的。
一
在读张柠近作《幻想故事集》中的短篇《罗镇轶事:六个乡下故事》时,我总是回想起舍伍德·安德森笔下那些居于温斯堡镇的小城畸人。罗镇人很像是《异想天开的人》中的乔·韦林,或《教师》里的凯特·斯威夫特,安德森写乔·韦林常常“被种种念头所困扰,而且在一念引起的痛苦中,简直难以抑制。话语从他嘴里翻滚踉跄而出……他一把抓住一个旁观者,便开始讲起话来了”。这不也正是罗镇人的日常吗?——农妇刘玉珍抓住医生,向他絮絮叨叨倾诉她的肚子不舒服、她的老公天天打她、她起早贪黑劳动、她与罗长生的婚事、她的女儿被镇长看上了……如我们所知,温斯堡人是在经历了心灵的顿悟之后开始沉默的,而他们之所以“顿悟”,则由于他们早已丧失了心灵交流的能力,所以温斯堡人才会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喧嚣吵闹,无边无际的“杂语”。这一点对于罗镇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杂语”同样开始于他们长久的沉默之后。
小说《农妇刘玉珍》里,在与刘玉珍、罗长生夫妇漫长的推拉扯皮后,做医生的父亲言简意赅地对“我”交代了刘玉珍的病情。这篇小说是如何完成自身的呢?当两人争吵到不可开交——杂语达到顶端之际,作者启用了一种独白的声音,简练地交代了以下几件事:罗长生知道实情后带着刘玉珍到省城看病;“三个月之后,刘玉珍就死了”。两件事只占文本四行篇幅,却强有力地收束了此前无休无止的喧哗,也似乎是揭开了那难以消融于日常杂语的深沉孤独。至于《流动马戏团》《嚎叫》两篇围绕着主人公“我”的叙事,则是将杂语式的孤寂引入一个特定时间坐标。前一篇小说以众人等待马戏团到来的一个上午作为叙事框架,其中穿插了许多乡间生活场景,少年的“我”忧心忡忡于一座不停生长的山峰,担心它刺破天空。故事最后,“我”因为知道自己沉迷马戏团的表演触怒了父亲,甚至想要离家出走。
《嚎叫》接续了《流动马戏团》的情节与后者的散文化叙事,但它又是围绕着特殊年代的父子关系加以刻画的。马戏团离开之后,因为父亲没有打“我”,“我”竟然感到自己像是孤儿,他甚至想要央求与父亲共事的药剂师来揍他一顿。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在故事开篇即已奠定,此后作者写道——因为这段描写实在生动,在此引述——“在父亲打我的时候,我一定会伴随着打的节奏大声号叫。否则,我舒畅和激动的感觉就要大打折扣。我想,我父亲的感受大概跟我差不多,我越号叫,他越激动,出手的频率就越快,力度也就越大。他同样伴随着打的节奏,还有我号叫的节奏,不停地喊叫,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父子俩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
其实,这段描写不仅胜在它的生动,还在于它准确地将程瑛一家的伤疤转移到了主人公身上。程瑛的父亲因写“反动标语”始终处在缺席的位置,“我”的父亲尽管在场,也难以和作为儿子的“我”正常交流,于是“我们”便只能用一种类似受虐与施虐的形式来表达爱——倘若这实难理解,也不过是因为特殊年代的爱无法诉诸言语——在这种特殊性背后,是“我们”每隔三年五载便要迁居,是少年的“我”为了引起父亲注意也沾染了暴力的嗜好。这种父子之爱的悖谬表达直至某一天父母失踪方告一段落,随后又以少年的“我”看到父亲被惩罚正式结束。
二
《小城畸人》写的是一个转折时期现代人彷徨无依、求而不得等等内心隐疾,《幻想故事集》却没有止步于此,或者说它没有止步于安德森对现代社会的控诉,作者实际上还给出了前者未能提供的一重视角。这个视角,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复活”。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与总体性》一文中,作者对文学的救赎功能曾做过如下表述:“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其本身,能够不被历史和其他学科门类所取代,一方面是因为它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带有拯救性质的‘奇迹’色彩。”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奇迹”是因其多解性与歧义性,能够为文学自身提供超越理性与命定的可能性。但除此以外,“复活”在《幻想故事集》中无疑还显露了它的另一重含义,那就是作者让那些絮絮叨叨的倾诉开始被人倾听,有人倾听,由此使得对话变成一种心灵的修复术。对话在 《小城畸人》中始终没有获得开始,畸人们从生到死拘禁在内心的顿悟与孤独的挣扎间,他们求助于乔治·威拉德之于事无补,正如杰西·本特利与柯蒂斯·哈曼牧师求告上帝无济于事一般。可是我们发现,在《幻想故事集》的最后两篇《黄菊花的米兔》与《普仁农庄里的女人》里,那种现代主义内在自省的唯我论——这恰恰又是此书第二辑《八个城市梦幻》的笔法——中遭到贬抑的对话,又一次被赋予了心灵交流的特权。
心灵交流,但不是为了真理;交流达成一致,也决非是求真意志在推动它们。这里实际存在着中西文明的差异:西方文明基本上还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框架,而东方文明追求的则是平等。真理从未抹煞个体与他者的差异,相反,差异是被真理制造出来的,而平等却将这种差异作为自身的前提。唯有从平等的立场出发,杂语才不致沦为失语,并且将会是一场双方都投入其中的对话。在《普仁农庄里的女人》这篇小说里,对话的倾诉者是李雨阳,倾听者是孔一梵,不过,在两人的交谈中读者分明还看到了这一文本涵盖的四对夫妻/情侣,也看到了他们的关系无一例外地经受着背叛的摧折。孔一梵是因为做“绿橄榄”直播网站的缘故,与高中毕业就来北京闯荡的万舒依结识。此后因万舒依做事没有章法,网站被勒令关停,孔一梵被迫与她分账分手。普仁农庄的经理梅萧华与她前男友也大率类此,他们也是在事业稍有起色的时候,其中一方情感出轨,与在北京游荡的考生潘修岚一拍即合;此后潘修岚终于考上美术学院的博士,又和王子得的本科同学、如今已在美术学院当老师的黄春丙勾搭上了,如此一来潘修岚便再次破坏了黄春丙与李雨阳的婚姻。
这四对夫妻/情侣的轨迹是如此相似,但这恐怕正是孔一梵能够以及愿意倾听李雨阳诉说的根底。同时,我也不觉得万舒依、潘修岚、陈曼娥这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疑流莺是作者试图抨击的对象:孔一梵与万舒依在一起时,他们“挣钱,数钱,吃喝,吵架,睡觉”,一旦孔一梵的网站倒闭,也就是他们感情结束之时;“以制造世界名家赝品”、“勾引艺术家”为生的 “考研党”潘修岚可以勾一勾手,就让王子得抛弃梅萧华、黄春丙抛弃李雨阳;至于李雨阳的弟弟李雨梵,恐怕更是至死都活在陈曼娥背叛的阴影中——如若我们将这条“现代爱情”的覆辙延伸来看,它无疑是指向了现代人的某种普遍境遇,这种境遇的真相此后也由李雨阳道出:“作为一位艺术型的文化企业家,一位身家过亿的老板,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亲人、生命、情感、信念,全部都灰飞烟灭。李雨阳说,她曾经大声呼喊:我愿意把所有的资产,全部交出去,换取我最珍贵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然而却毫无用处。我这才知道,什么是‘叫天天不答,呼地地不应’。”在传统社会,什么事情、任何价值都是确定无疑,而试图挑战它的尝试终将归于笑柄。现代社会则不然,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那位曾经抱着农耕时代信仰的李雨阳突然领悟的事。
三
怎么办?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小说的四对夫妻/情侣面前。孔一梵选择飞往“小资撒娇圣地”丽江做“心灵疗伤”;梅萧华回到丽江,应聘进入普仁农庄工作;李雨阳是被丈夫黄春丙送到丽江修养——请注意,小说在这时还没有提供一种文学才能创造的救赎,虽然此前文本中也曾闪现过一次“复活”的字眼,但那不过是媚俗的生活情调。然后便是这几个人的相遇,他们开始围绕着李雨阳——这个自称是“死过一次的人”——进行一场看似无尽的谈话。附提一句,至少从这篇小说,我们看到了一种双方都严肃持守倾听之美德的对话,是如何具有它的伦理意义与修复功能的。通过李雨阳的倾诉,孔一梵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真正的复活正在来临,这复活同时也源自她到丽江之后结识的纳西族女人木莲枝,她将其称作“木妈妈”。木妈妈陪着李雨阳哭,陪着李雨阳笑,尽其所能地让后者吐净心中郁结。木妈妈还时常用纳西话唱歌给李雨阳听——举凡这些情节,都像是以儿童目光去重新打量这个早已失去童年的世界,也无疑与前文的叙述构成反差,但这又是我们此时此刻能够设想的唯一救赎之途。
这种救赎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启迪,是精神的焕然一新。诚如故事最后孔一梵发现与理解的事:当李雨阳面对着路边的花叶草木喃喃自语,“为一片叶子的新生而欣喜不已,为一个花瓣的衰落而悲伤落泪”时,她真的改变了。造化的力量与生命的奥秘,如今重新从数字、抽象的景观与熟视无睹间转向我们,对我们开口,而我们也将转向他人开口。以此观之,这篇小说的线索也正是《幻想故事集》的内在脉络,从《罗镇轶事:六个乡下故事》的杂语,到《幻想故事集:八个城市梦幻》的失语,最后到《旷野集:三个女性故事》中的对话,我们一步步地看到那些已经成为“失语”的“杂语”是如何重新舒展成为“对话”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刘玉珍死于无人理解与无人倾诉的孤独,但李雨阳毕竟经历了一次复活:她“重新活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