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镇电影院》:朱山坡的童话
来源:文学报 | 叶桂杰 2019年05月31日0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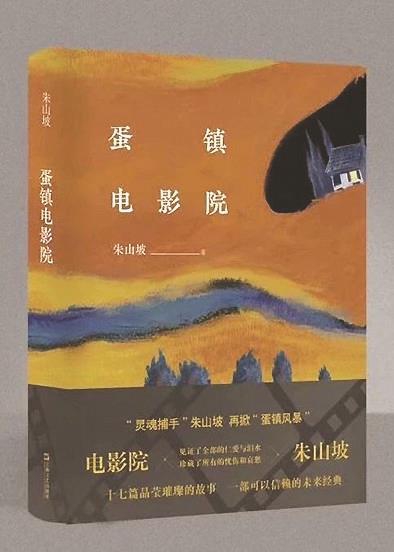
《蛋镇电影院》朱山坡/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就从作者对余华的崇拜说起吧。这是作者毫不讳言的。作者不讳言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承认自己写小说是“半路出家”,以及读书量并不大,等等。我们知道,自曝缺点和自矜自夸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们皆是异己之力量。然而对于某些自身缺憾的“不讳言”,因为取消了“刻意”,而显现出自然、可爱、真诚的品质来。作者即是如此。
因为以笔者对他的了解,他似乎从不介意成为偶像的影子。这样谦逊的性情,如此平和的姿态,是比较可宝贵的。但事实上仅凭这一点,作者的写作与余华的写作就悄然发生了分离。以作者2016年7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为例,就可见其一斑。小说中蹦蹦跳跳的小镇居民,说着一些幽默不足、俏皮有余的荤段子,打着一些智量不足却自得其乐的小算盘,同时还像《兄弟》里的李光头那样,调戏小镇里最美丽的“村花”。这一切调性看起来与余华是多么的相似,但仔细一琢磨,却又不尽相同。其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作者叙事的“身高”与小说中芸芸众生的“身高”是相等乃至更低的,因此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得以感受到叙述者参与文本狂欢的积极性、自觉性,同时发现叙述者并不在意对自身促狭、算计和狡黠一面的坦白。
与《风暴预警期》相比,作者新近出版的这部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同样是以“蛋镇”为叙事空间的,并且,后者并没有把蕴藉于前者的“焦灼与躁动”的心绪抛却。作者大约心里比较透亮,即恰是这个主题使得作者有了有别于他人的写作特质。在“蛋镇”的世界里,传奇是没有的,英雄是阙如的,大悲恸和大欢乐也难以见到,一切都归于日常、琐碎和计较。但我们千万别急着下判断,以为这样的叙事便是平庸无趣而不足道的。事实上,它的有趣和欢乐即在于此。考诸“蛋镇电影院”,可知宏大的话语与贫瘠的现实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就在鸿沟里,梦想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欢脱与哀伤、焦灼与躁动亦由此诞生。
习惯了强节奏、强声音、强思想、强逻辑的读者,再去读《蛋镇电影院》,或许会有些生涩。因为在这里,目之所见尽是些小打小闹、小争小吵。譬如《在电影院睡觉的人》,讲的就是一个恪尽职守的粮仓保管员为了弥补缺觉而特意跑到电影院睡觉的故事。诸如此类。这些个故事,略知其内容,便给人以难登大雅之堂之感。它们仿佛是作者在文字背后,眯缝着一双小眼睛,嘴角撇着,笑嘻嘻地逗趣你,用不安分的手指勾你、挠你,给你讲些个段位不高但自拟还行的逸闻趣事,令你想听又不想听,想笑又觉得掉价。然而,无趣但令人喷饭的尬聊,在《蛋镇电影院》里却是所在多有。所以习于庙堂之高、不屑江湖之远的读者,是不大容易接受的。若要领略其间人间烟火之气,唯有松弛紧绷的心弦,降低高昂的视线,解开领带,换下西装,脱掉皮鞋,方可得之。
本来我们以为自己是纡尊降贵来观赏闵彩虹、卢大耳、袁独眼们的闹剧的,可是一旦在“蛋镇电影院”里闲逛一圈后,才忽然发现那不过是自己的幻觉。在这个“鸟蛋”一般大小的小镇里,镇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快活,何等的自足。他们在物质、钱财均匮乏到令人震惊的情况下,对生活依然葆有昂扬的心态。毕竟,电影作为一门以影像为媒介的虚构艺术,不仅是进入到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片时空的快速通道,更是对贫瘠现实的超越:蛋镇人民虽然身份地位无不卑微到尘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刘晓庆、邓丽君、叶玉卿、山口百惠的崇拜;在他们粗鄙的行为、混乱的逻辑下,潜藏着对温柔、善良、娴雅、责任和美的不懈追求。
书中,关于一个电影院售票员胖子的故事,是特别显著的例子。一个从小生活在闭塞的小镇里、连生存问题都尚待解决的电影院售票员,却怀揣着一个到美国去的想法,这不得不让人感到荒唐。在因此遭到整个蛋镇的嘲笑后,主人公胖子章居然毫无愧色。主人公很是笃定。他气定神闲地说:“我干这个工作是暂时的,我要偷渡去美国。那是早晚的事情。”把这个不便见人的“秘密”摆到明面上来言说,立即就显出缺少城府。于是当他“被问得烦了”以后,便赌气似的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这些井底之蛙一起。”这话说得就有些无赖了。无赖的背后,却是不被理解、只能自我激励的心酸和无奈。然而通过这个事先张扬的秘密,我们仿佛忽然窥见了蛋镇人民隐秘的内心。试问谁不曾做过各式各样的梦?或者曾经,或者现在,或老或少,都有。只是有些人敢于直说,有些人羞于示人罢了。
由此可知,是人性中尚未寂灭的品质,照亮了“蛋镇”。我们原来并不知道,“蛋镇电影院”的底色竟是晦暗而沉重的,那些欢乐,皆是虚假。像猴子一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蛋镇人民,到底掩不住内心的悲楚和欲念。他们渴望从灰色的蛋镇逃离出去,拥抱璀璨而辽阔的大千世界。那植根于人类基因深处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泥石流般汹涌的“力比多”,是如此浩荡地繁殖着,如此迅捷地代谢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调动夸张的肢体和巨大的口腔,来帮助消解、消化、释放。(这也难怪,在《深山来客》里,“看电影”被鹿山女人顽固地认为具有“治疗贫血症”的神奇效能。)
有时候我竟怀疑,关于“蛋镇电影院”的故事纯然是一种虚构。它们乍看起来仿佛贴着现实的沥青路铺陈而去,文字间弥漫了潮润的地气,但却与土地和现实全不在一个呼吸的节奏上。我甚至猜想,所有平庸无奇却生机勃勃的故事,所有蛋镇电影院里的欢乐与忧愁,无非是作者对美好的玄想,对乌托邦的编织。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蛋镇电影院》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毋宁更确切地讲,是一部“童话故事集”。
而在童话的意义上,作者又回流到了他的精神导师——余华的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