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18年11月09日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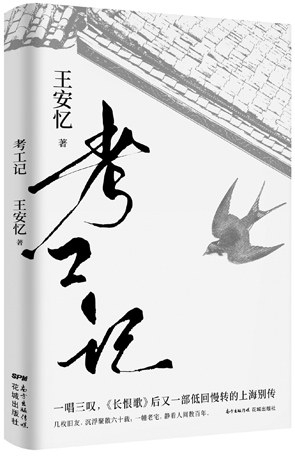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考工记》出版之前,王安忆曾考虑过另外一个名字,叫“老友记”。
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各奔东西。陈书玉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老宅最后的“修房计划作罢,大木匠也走了。事情兜一圈回到原初。后进的房屋全塌了。这宅子日夜在碎下去”。小说中大虞去世后陈书玉在他棺前地上的一坐,令人潸然泪下。
“老友”虽是情节的重要部分,王安忆最终还是觉得“考工记”有古意,辐射也宽广些。《考工记》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这部写老宅命运、写上海“小开”的命运,为什么也叫《考工记》?看完书,我最感到疑惑的,就是书名和内容是有些吻合,但并不完全吻合。
王安忆:《考工记》当然是借用古代营造工艺官书名无疑,就像小说《长恨歌》的取名法,从字面看,故事以老宅子颓败修葺为线索,同时隐喻人在历史变迁,时代鼎革中不断修炼,终成结果,应是切题的。
中华读书报:历史风云在小说中只是背景,往往一笔带过,但是读者已经一目了然。如此淡化时代背影,这样的处理方式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安忆:小说中人物可说穿越时代而来,不能说“一笔带过”,实实是当锣面鼓,每一时间段都迫切应对,压力重重,扭转生活走向,历史在个体命运中的体现不像教科书上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我不同意所谓“背景”的说法,而是前景,或者说是整体的情节。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了几位上海小开,但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开又完全不同,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规矩、有抱负的上海青年,不止是对各自的人生有脚踏实地的追求,对待女性也有礼有节。尤其是陈书玉,他心中的偶像是冉太太,遇不上那样的人,宁可选择独身。这样的一群上海青年,有多大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王安忆:“小开”是上海坊间对老板的儿子的称谓,就像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和草创天下的第一代不同,他们生活优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都会城市西式生活方式里,培养了绅士风度。陈书玉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人,进入新时代困难重重,冉太太于他不止是“偶像”,更是同时代人,他终身未娶,还因为目睹周围,生儿育女简直是“造孽”。至于“典型性”和“代表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主张“四个不要”,其中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典型性”,我更重视个体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几个女性形象,美好而生动,大虞的乡下女人,“胆壮,不畏前畏后”,朱朱的夫人冉太太的风范,即使丈夫被关进监狱去求人,也无“卑屈之态”;学校的女书记,一个经历了战争的女人在陈书玉心惊胆战的时刻送他“不卑不亢”四个字……女性在您笔下总是自强自立,在狂乱世事中独挡一面,性格心理着墨不多,却跃然纸上。就想,在写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您的心里也应该十分强大并且满怀美好吧?
王安忆:我倒是无意识在这一部小说里树立女性形象,若要论及这一点,大约出于惯有的意识,女性比较男性适应度更高,我母亲有一个观点,说男性很硬,像钢,但一折就断,女性呢,就像蒲草,很软,但是柔韧,百折不挠。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弟弟”,不是奚子的弟弟,只是一个称呼,小说中也始终“弟弟”称呼,而“弟弟”的多处出现,又总是重要的场合,有着重要的见解,“弟弟”在小说中承担着引路人的角色。但描写也比较含糊,有一种神性的气息——是有特别的用意吗?
王安忆:小说是世俗的艺术,它要求现实的合理性,要让陈书玉在新社会立足,需要条件,所以就必须创造机会,为他开辟通路,“弟弟”是一顶保护伞,同时,他随“弟弟”一行去大后方,再一个人回家,就有了和老宅子独自相守的时间,于是,开始了终身为伴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婚姻大事还是老宅的处境,小说里多次出现“顺其自然”。这也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是否也是您的一种人生态度?
王安忆:所谓“自然”,其实是不可抗力,风云变幻,连“弟弟”这样接近政权核心的人物,都不好说个定准。然而,在这不可测之中还是有所测,那就是——“变”,小说中人自有走向,不能简单视为作者的代言。
中华读书报:《考工记》很多叙述含蓄,而且结构紧密。这样的叙述手法,您是希望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吗?
王安忆:这是小说者的本职,写作的时候,不会那么自觉地选择什么“手法”,也不会考虑给读者什么效果,而是因势进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多少有一点命运感。
中华读书报:为了维护老房,陈书玉收拾补不胜补的破绽,甚至在台风来临的时候索性扑倒,像蜥蜴一样压在被狂风掀起的油毡上。读到这里特别感动,陈书玉对老宅、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和维护,却最终因家人索要赔偿得不到完善的解决拖延下来,结尾“那堵防火墙歪斜了,随时可倾倒下来,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这么写有何隐喻吗?
王安忆:从广义说,小说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隐喻的,狭义上则具体事具体分析,说它“白旗”,首先是由事实规定,因墙面是白的,小说方开场,陈书玉走近老宅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面白色的墙,最后当它作“白旗”,一是老宅在塌陷,另外,多少有一点降将的意思。
中华读书报:这几年您的写作,无论是《天香》还是《考工记》,都有古典文学的气息,写作的内容,也都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各有侧重,比如《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描写晚明时上海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的背后,其实也有一点对上海资本主义化的反讽。而《考工记》在追寻城市发展史的过程中,更有“眼看着楼塌了”的无限悲凉。能否具体谈谈,《考工记》的写作对您而言,有怎样的挑战或意义?
王安忆:我好像不觉得有悲凉的情绪,《天香》的“眼看着楼塌了”,同时眼看着四野盛开,赵昌平先生评论《天香》,有句子:“莲开莲落,而又化身千红”,就指这个吧!新旧更替,是历史规律,《考工记》写的还是人,那老房子迟早要夷为平地,即便重建,也是当旅游景点,就已经是个变通了,我不惋惜。
中华读书报:在一次又一次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写作中,您获得了什么?
王安忆:我想最好不要用“回望过去、追溯历史”的概念来解释我的小说,从叙事论,小说永远是在写过去的时间,当然,科幻小说除外,我想,发生在50年内的事情,就不能成为历史,再则,《考工记》截止的时间已是两千年以后了;再从文类分,历史小说当是指历史事件的写作,《天香》写的依然是日常生活,只是年代久远些,我还是个现实主义者,贯穿我写作经历过程,至今未改。
中华读书报:您的写作越来越节制了,举重若轻。比如写冉太太和陈书玉之间的感情,再多的惦念和关心,也是不显山露水的;比如写陈书玉和大虞等比兄弟还深的感情,也是节制内敛的。这和您以往的写作也大有不同。您觉得呢?
王安忆:确实,我写作越来越挑剔,希望有更好的细节,尤其语言,不容易使自己满意,我的要求是,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书面,所谓“俗”就是口语,冯梦龙整理的《山歌》《挂枝儿》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中华读书报:书中有一小节,涉节陈书玉家里窨井的一面铁盖,铜铸的空镂,一个散发女头像。这铁盖到底有何来历,陈书玉各处查询均没有找到答案。我在阅读中其实也希望有个答案,但是读完也没有发现就想,也许这里正另有暗指,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一处老宅藏有这么多稀奇珍贵的东西并不以奇?很想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
王安忆:谈不上“博大精深”,我只是想表示,上海这地方,华洋杂居,东西汇合,实际上没有什么根基,那老宅子并不是特别宝贵的文物,但在近代城市上海,却是个稀罕物,它的风格也是混搭。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陈书玉和阿小的对话很有意思,似乎也在回答一代人的疑问:诸如如何解释人人都要留城,将乡下当处罚?诸如为什么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说中处处暗含类似的玄机,作品并不太长,越读却感出她的厚重。这里,承载了您对于城市怎样的思考?
王安忆:阿小是陈书玉的年轻朋友,因校长的关系,也因时代缘故,他也要吸收新鲜的因素,我还交给阿小一个任务,就是推动陈书玉修葺老宅。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天香》和《长恨歌》有一脉相承之处,是将笔墨重点放在女性成长历程和心灵史上,《考工记》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遍地枭雄》中上海男孩韩燕来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都市边缘人的抗争和宿命。多年来,您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不断带给读者新的阅读感受,是不是胜券在握?
王安忆:《考工记》和《遍地枭雄》在我的写作里有点例外,那就是写男性,我的小说大多以女性为主,男性人物不是所长,但这两个人物的特质已经远远超过性别的规定,再要纠正一点,“韩燕来”不能算作社会底层,恰恰是曾经的小康家庭,在城市扩大化中失去土地,他属于阶层更替中的失利者。我没有去“突破”什么,我一直延续写实主义的路数,从来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只是努力向好罢了。
中华读书报:对于写作状态及节奏的调整和把握已经非常自然成熟,您觉得自己还存在写作的难度吗?上次关于《天香》的采访时您谈到材料的把握对自己构成难度,现在是不是有所突破?
王安忆:材料是永远的问题,非但不可能突破——因为它和处境有关,而且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严苛,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可能对自己的期望在提高,对小说的期望也在提高吧!不像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写成小说,幸而在那时候已经动笔,放在今天,也许就不会写了。到哪座山唱哪支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