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作家是一面镜子
来源:北京晚报 | 张玉瑶 2018年08月17日09:07

作者简介: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文化随笔《小山河》《绘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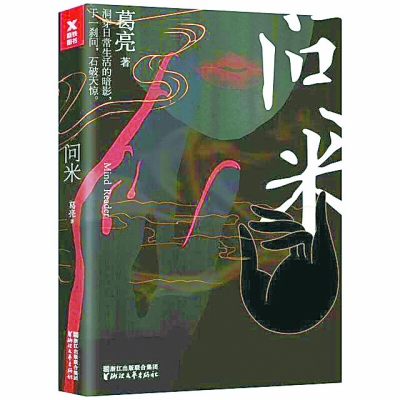
有人说葛亮有颗“老灵魂”。说法不知从何时起,大约来自他这几年最负盛名的小说《朱雀》和《北鸢》:年轻作家难得有这般耐心和笔性,打磨古典词句,细细摹状旧时人情风物,打捞湮没在民国烟尘中的古都往事。见到葛亮,提及此,他笑言:“那你接触我,觉得怎样?”——似乎又难一言以蔽之,眼前的他分明入时、敏锐,言谈举止颇有西方风范和都市气息。葛亮点头说,对呀,一个人是一个综合体,一个作家也有不同的面相,一方面在观念里接受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城市里,有对当下的挖掘。
最新的小说集《问米》出来,就有记者问葛亮,是否要“转型”。人们印象中的葛亮是《北鸢》里的葛亮、“老灵魂”的葛亮,《问米》里一系列小说背后的葛亮却面目多端,突破了古典的范式,时而惊悚,时而悬疑,时而诡谲,时而绮丽,纷纷披了都市的面纱,魑魅魍魉,魔性万端,异化人的心魔纷纷而来。葛亮说,其实这些小说在写作时间跨度上和《北鸢》是差不多同时的,只是书次第出来,容易让人误解。在他看来,只是代表着自己写作的另外一个面向:如果说《北鸢》、《朱雀》等衔接着他对祖辈致敬的立场,反映了从历史到当下的完整轮廓,那么《问米》就更多切入的是对当下和内心的叩问,每一篇都代表着他对当代社会认知的某个层面。就如第一篇《问米》里的通灵师阿让,每个人都能通过和他的交流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一面折射世间千万情状的镜子。作家也是一样。葛亮说,这种种不同面向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他。对于读者来说,《问米》的风格或许意外,但他珍惜这个“意外”。
与之相应的,是扑面而来的充满陌生化的语言修辞和氛围意象。《问米》里有七篇小说,每篇的标题都是一个意象,问米、罐子、鹌鹑、朱鹮、龙舟、竹奴……葛亮擅长从意象出发,结撰起他的故事。他的人物总被他置于某些非常态的境遇下,突破了波澜不惊中的蒙昧和不自信,生生逼出内心或正面或邪恶的小宇宙。
葛亮生于南京,后赴香港求学,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与中国作家普遍擅写乡土不同,他的写作中映照着五光十色的城市魅影。从《朱雀》的南京、《北鸢》的天津与上海,到《问米》,则遍历东南亚、岭南、西北、香港等等,无意间为他所谓“没有结论”的现代城市拼了一块版图,留了一份当代人需要间离观看的影像。
或许和文学教授的身份有关,葛亮爱提及审美的概念。采访结束时问他,在他这些题材迥异风格多变的作品里,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内核?他想了想,依旧给了一个审美意义上的回答:对文字的要求——“文字的表现形式不同,气韵构造有异,但我对文字本身有一个标准,无论任何题材,都坚持审美的取向和趣味。”
喜欢悬疑小说的作家
《书乡》:《问米》很有悬疑风格,你也在后记里写到悬疑小说对你的吸引。悬疑小说作为类型文学,多数时候在主流文学圈中是不获首肯的,但你似乎没什么偏见。它何以打动你这样一个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家?
葛亮:我们对悬疑小说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成见,认为它注重逻辑的密度而牺牲了对人性、对社会背景和语言审美的考量。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小说家横沟正史,从他身上,我看到对本格的执迷并不一定以牺牲其他元素为代价,他就能将各方面比较好地融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小说的故事内核是重要的,它和形式之间并不矛盾。而故事的逻辑恰恰为我非常注重,悬疑小说在这一点上很打动我:本格推理步步指向结果,其实也是指向人性。只是悬疑小说所揭示的人性面目通常是非常阴晦的,这点我不十分认同,我认同的是它逻辑所指向的一种审美的意义,一种“造境”,就好像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间谍。我在《朱雀》中也写到一个美国间谍泰勒,便是借用了推理小说元素,构置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自在体”:他热爱中国文化,又担任间谍工作,一方面从家国民族立场有背离,另一方面内心却经历着煎熬。
《书乡》:悬疑小说往往会陷入为悬疑而悬疑的机关当中,但你似乎有意在超越,比如《问米》这篇,在神鬼的外壳之下,落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悲剧上来。在平衡悬疑性、惊奇性和真实性、现实性上,你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葛亮:我们一直以来觉得本格推理太过硬,就像一个方程式,由因必然导致果,这恰恰是我在这部小说里特别警惕的,我不想让人感到严格的甚至严厉的构造方式。所以你看到这本小说里虽有推理的外壳,但结局有的让人意外、有的荒诞,都不是非常严谨的本格逻辑应当达到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人的无力感诞生的来由,我们作为平常人甚至庸常人,当被置于一个非常的情境下,每个人所能爆发出的张力及其带来的效果都是不能预想的。
这里面最接近本格的是《朱鹮》。我以《朱鹮》作为整个系列的结尾,其实也是一个致敬,来向读者表明我心中的本格是怎样的。这个故事的破案过程以“我”作为线索,而最后嫌犯是“我”,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在破案过程中,“我”在不断伪装和拷问自己。这是超越伦理、道德、法律的情感,不能用任何一些规则去定义,这也就打破了本格的界定,是我想要的。
《书乡》: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因你同时写长篇和短篇,你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吗?
葛亮:短篇小说更像时代和生活的横断面,其意义在于,提供你的灵感以一个突然释放的空间。短篇是可以围绕一个灵感来写作的,就像《问米》里,是一个通灵师瞬间打动我。长篇则因为年代跨度,需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对历史的感知,价值观、世界观和很多一系列的细节。短篇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要产生一击即中的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意象。你看我每个标题都是一个意象,中国语言审美讲究言未尽而意已达,我尝试与读者分享这些可以回甘的东西,我相信我的读者都非常聪明。
《书乡》:在语言层面上,你也有多幅笔墨。《北鸢》的语言非常古典,《问米》里则有更加多样的呈现,你如何去打磨和寻找合适的语言形式?
葛亮:写作本身是一种翻译,或者说转译,由不同的语言转译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典型表现就是《北鸢》,不仅是在反映时代,也是在转译文化。民国时期的文化气象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专门打磨了一套语言,不是单纯白话文,也不完全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语言,而是找到一种二者互相渗透的结合体,既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气韵,也符合当下读者对语言的审美,能让他们接受。
尝试用不同语言写作是我的习惯,也是一个小说作者必须面临的检验和考验。你不能想象用精致典雅的吴侬软语去表现《问米》里那个带有一点粗粝、痞气、但有好奇心和悲悯感的角色,所以他是个北京年轻男人。当他遇到通灵师阿让,阿让是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对位。
书写“没有结论”的城市
《书乡》:你是南京人,后来长居香港,但你的小说中有更加丰富的地域性。很多作家一般只写自己熟悉的城市,但你好像没有太大的障碍,对各地的语言风俗都能做到熟习,这种跨越地域的写作是有意识追求的吗?
葛亮:你读得很仔细。这些篇目是我在十年里写的,其间我去了很多地方,会深深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冲击,从而刺激人生的某一个面向。《问米》就是因为我在河内遇到了这样一个通灵师,他的生命历程当然没有那么传奇,但给了我一个启发。如果不去河内,我就不会写这个小说。《罐子》里的侉叔是隐姓埋名逃难到岭南的西北人,北方是土文化,安土重迁,南方是水文化,这中间就有一种砥砺,我想写出这种砥砺。如果二者不碰撞,就不能体会到铁汉柔情,以及对历史的回魂有怎样的应和。《竹奴》是一个温柔的故事,氤氲着南方水气。这一方面是审美的考量,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因子,塑造着不同的文化呼应,借由这样的呼应,人的多维度和丰富度就出现了。
《书乡》:之前采访过一些主要写乡土的作家,他们有时会表示,写乡土容易,写城市却常常把握不住,但你笔下的城市故事都游刃有余。张悦然说,你扭住了现代都市中人的心魔,这种“心魔”在你看来是什么?
葛亮:应当是来自当代人的不自信。乡土是中国文化生长的渊源,在我们的审美体系和价值观上,认知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但到城市写作境遇中,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再连接乡土中国传统,而是移植了新的西方价值体系,使得人心产生了更加大的驿动、浮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所以说当代城市在写作层面上的难度是相当之高的,因为它没有结论。
《书乡》:那么你觉得城市文学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葛亮:我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常与变”(笔者注:出自沈从文《长河·题记》),所以我为什么喜欢沈从文先生,虽然他也是在写乡土,而且不喜欢城市,但他非常精准地抓住了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在变迁中的社会最基准的东西。在我的城市书写里,我也不仅仅去写最fashion(时尚)的东西,也很注重它们和传统的连接与砥砺。中国的城市生活有特殊的根基,和西方不一样,符合西方现代城市建造意义上的大陆城市只有一座,就是上海,而北京、南京、西安等都是以都邑为基础发展的,所以写中国城市也就没法回避“常”的那一面。在我们的城市背景中依然是有乡愁的,就像我在《北鸢》里写到天津,和上海的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书乡》:香港应该和上海是一类城市吧?
葛亮:香港反而更加有乡愁,因为它的本土化历程更加艰难一些。上海人觉得自己之所以作为一个上海人,是他与生俱来的现代性。而香港在被殖民的历史中,非常强调本土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呈现为一个土洋结合的文化形态。
文学研究者的最强逻辑
《书乡》:《问米》、《不见》、《朱鹮》等很多篇都涉及了戏曲元素,你本身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吗,是否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滋养?
葛亮:我挺感兴趣的,我家里几代人都是票友,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等,我的了解明显不如他们,也不敢自居为一个票友,但他们给我很多指点。戏曲一方面代表我们传统文化的部分,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借由相对简洁的方式,表达复杂的人性和时代的综合体。中国戏曲最令人着迷的在于它的这种写意性,这和我对文学和文字的审美是一致的。
《书乡》:小说中也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职业,包括动植物甚至理工科等等。这是平时的积累,还是为写小说有意识地查找资料?
葛亮:两方面都有。我父母都是理科的教授,我爷爷在大学教艺术史,对我这方面有一些启发。《不见》中杜雨洁母亲的形象有一些就来自我的母亲,她是数学教授,日常也习惯说把什么数目Σ(数学中的求和符号)一下,觉得比把什么“加起来”更带劲。职业会植入到对生活的理解。小说家需要表达不同的人,就像卡佛说,好的小说家,对日落和旧鞋子都会充满了好奇。不同人的思维模式对同一件事的反映结论可能是不同的,反映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想表现的恰恰就是这种差异性。
《书乡》:说到职业,你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这重身份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葛亮:最近被问到这个问题四次了,真的很重要吗?(笑)首先这个身份不是负累,否则我早就辞职了。人们总有某种成见,认为研究者思维是理性的,小说作者是感性的,但对我并不是这样,两方面我都很受益。学术训练对写小说是有帮助的,提供了脑力上的激荡和交流。比如长篇小说里这么多人物,我从来没画过一张人物关系图,却不会写乱,所有人物都会在我脑子里,有来处有去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研究者身份带给我的一种逻辑感;第二点就是做案头。案头工作对研究者非常重要,不仅仅是fiction和non-fiction(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不是说非要做史料,而是做这些会让你有底气;第三,作为研究者需要做一些田野考察,深入人群,这对写作大有助益。比如我和老辈交流,最着迷的一点就是,他今天讲的和昨天讲的不一样。作为研究者会困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严谨,但作为小说作者,又会觉得带来了文本的开放性。这种双重身份对我来说产生了某种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