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我走了一条歪路
来源:北京晚报 | 陈梦溪 2018年04月16日07:39

马原在他的图书馆看书

《牛鬼蛇神》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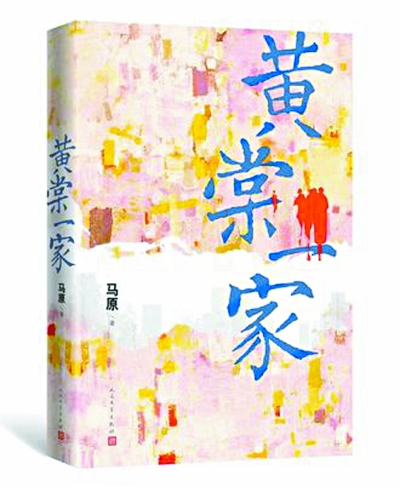
《黄棠一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这辈子在别人眼里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得了大病敢不治,比我小说写得怎么样重要地多。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随性,我可以做任何任性的事情,大多数人成年后其实就没有了任性的权利和资格。”
一个一生随性的人
书乡周刊:生了病却不接受医学治疗,从大城市跑到山林间,你做了一个很大胆的选择,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你。今天再看这个选择,你会怎么说?
马原:我这辈子在别人眼里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得了大病敢不治,比我小说写得怎么样重要地多。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随性,我可以做任何任性的事情,大多数人成年后其实就没有了任性的权利和资格。我这辈子和别人最大的不一样其实在这儿,不在其他的方面。可能在你自己的粉丝中你是半神半人的角色,但是在自己生活中什么最要紧呢?就是随性。一个一生随性的人,活地一定比那种看人眼色、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人要舒服地多。而且我敢放弃在上海优越的生活、很好的社会地位、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来到山里面生活。
书乡周刊:一开始你选的地点在海南,后来才找到这里,云南有哪些比海南更吸引你的地方?
马原:海口我有好几套房,常住的那套是真正的海景房,270度海景,三面环海,景色特别美。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更喜欢山。在海口我就没觉得那是我最后的归宿。当然海口的几座大山我都去过,五指山、尖峰岭等等,但是没有特别中意的、可心的地方。2011年春节,我偶然走到这,看见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儿我上辈子来过。我要找好水,怎么判定哪的水好呢?我想好茶是好水养出来的,我重点找过几个茶山,我去过安溪和武夷山,武夷山我特别喜欢,但那里属于福建北部山区,冬天太冷,不宜居住。在这种地方落脚,得心特别静,特别宅才行,不然受不了这个寂寞。我们想找个保姆,保姆都觉得寂寞,待不下去。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为这个泉水我多花十万块都愿意,因为我有自己的泉水,我的邻居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赚大了。
书乡周刊:换水这个理论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受别人或书上观点的启发呢?
马原:是我自己的。我觉得患了病的身体就不治疗了,当你得了治不好的病的时候,从哲学上强治一定没有好结果。现在得了治不好的病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强治,结果都很惨,一个是病者受罪,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离开,没有离开的那些也都维持着很不好的状态。这两年对于生命质量的讨论很多,很多人都提出活着的时候有点尊严,不要插了无数的管子,最后却是奄奄一息,只剩半口气的状态。
书乡周刊:花姐对你“放弃治疗”的态度是怎么想的?她支持你吗?
马原:花姐的性格是那种示弱的人,绝大多数人是要强的,但她不一样,她示弱,跟我特别和,我们结婚11年了都没吵过架。有时候我高声几句,她就不说话了,过一会儿说,老公别生气了啊。女人不就这样嘛。她示弱你有什么脾气啊。但其实花姐内心是个无往不利的人,但她以水的那种性格和人相处,我有棱有角,但她绕开我。所以我生病选择不治她也挺支持我的。她内心很强大,我之前遇到一次意外,她一点都不怕。
书乡周刊:你指的是刚来这里建房子的时候,被一群当地人打伤的事,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过?
马原:嗯,深夜来了一群小伙子,上来就打我们,她一点都不怕。我事后问她,你真不怕吗?她说真不怕,你们要打我老公,我就是拼了命也跟你们没完。但是平时见到一条蛇她都会尖叫。我生病一开始叫她离开我,不想拖累她,她觉得生病不是什么问题,遇到大事她一点都不慌。所以我生病是有她在背后强大的心理支撑。
书乡周刊:你在文章里说过你们每天都在谈恋爱,用现在的话就是秀恩爱。
马原:花姐没读过什么大学,没有读过什么书,认识我之前,她一本书也没看完过,对看书也没有兴趣,但是她是个很包容的人。我认识她这11年来是我这一辈子过得最好的生活,写东西写得最多的时间,而且在这11年中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我今年66了,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生命是跟花姐在一起的,这六分之一的生命长度里完成了我写作作品的一半,我最大的幸运是遇到花姐。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儿子马格,他是个特别可爱、特别漂亮的男孩,他是带给我们快乐的源泉。
同行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
书乡周刊:你关注新一代的写作者吗?
现在很多我们称为作家的年轻一代创作者都不怎么写小说了。
马原:其实就是当明星。我和张嘉佳、刘同是同一个职业吗?你们可能还把写书的人叫作家,但我早就不说“作家”这个词了,我更愿意用“小说家”。小说家和广义的作家不是一个行当,虽然我们也一起参加过文学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做的事情从本质上不一样。小说是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一个好的小说家一辈子要创造几十个人物,写出几十种人生,有的长、有的短,有的两千字,有的两百万字,但他是在不断造人、造人生的过程。这和美食、游记、杂文、随笔是很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也不觉得写小说一定比别人做的更高明一等,但是我们小说家做的事情比别的作家做的事情更有趣,有原初的味道。小说家是个“无中生有”的职业,其他所有的写作都是“有中生有”,单就这一点就不一样。
书乡周刊:你是单纯享受那种创造命运的乐趣的人,你创造的哪个人物最奇特?
马原:我一辈子写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叫“姚亮”,我把他定位成一个男人,一个随着我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男人。当然我会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也有观察身边人的经历,但是整个人物和关于他的故事都是无中生有的。这和报告文学、传记、非虚构的路数差别很大。说心里话我特别爱我的职业,懵懵懂懂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职业,最初是阅读,接着照猫画虎,一晃就一辈子,几十年这么过来了。说老实话,我算是我们这个行当里特别幸运的,一辈子写虚构的东西。
书乡周刊:你没有曾经尝试写一些纪实类的东西吗?
马原:其实曾经纪实文学大行其道,但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非主流”的作家。就是这么一个边缘的写作者,留下来了。我写了四十多年,到今天还有读者,还在一本书一本书地出。我们那一代最红的一些小说家,现在作为小说家早就不被阅读了,他的创作早就过去了,因为不再写了。开始写作的时候红透了,慢慢地就改弦更张了。这是一类作家。还有一类,比如陈忠实,是比我大一辈的作家,是我们的兄长,但他在《白鹿原》获奖之前在文坛不是一个重要的作家。最近的例子是写《繁花》的金宇澄,在他被大家熟知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此前很少人听说过他。我这一代人里我算是最没出息的,我没得过任何奖。
书乡周刊:是说你没拿过任何重要的文学类奖项?
马原:不能说完全没得过,十月曾经给我了一个十月文学奖,但是大一些的奖都没有。我年轻的时候没意识到,我们写书原来求的是书外的东西。我其实走了一条“歪路”。从成功学这个意义上,同行里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我。因为我在学校做系主任,会面对各种的考评和成绩。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写小说不算科研成果,评论这篇小说算科研成果。就是说,我写了《纠缠》不算科研成果,你写个《纠缠》的读后感就算。
书乡周刊: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对自己的“不成功”是不满意的。
马原:我在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确实不是在为了自己不拿奖而自卑,其实反而是一种自傲。我很为这个自豪,这个就是我写小说一辈子的信念和理想。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跑偏了,后来发现是我跑偏了,我掉到管道里去了。
我是拒绝改稿子的
书乡周刊:去年底新出版的这部《黄棠一家》里写了很多新近的新闻事件,包括微博的一些事情。
马原:其实这个小说是我2013年写的,我同时写了两部长篇,没着急往外发。《黄棠一家》的发表就出现了障碍,《花城》要去了一段时间后就告诉我需要删,我不肯删,我说要不就不发了。我很不开心,他们一删我就弄得兴趣特别寡淡,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纠缠》就出得特别顺利。后来碰到了孔令燕,她看了之后决定要出书,我在写了四年之后才有出版的机会,她是以出贾平凹的小说闻名的,贾平凹大部分小说都是她出版的。他们曾经有一些修改的意见,我跟她说,你可能不够了解我,我(的小说)是不改的,认识我的编辑都知道,我是拒绝改稿子的。
书乡周刊:你和贾平凹先生都属于一直在创作和出作品的作家,他也是每一两年就出一本新小说。
马原:我和他其实写作路数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主流作家。从印量上讲,他的每本小说20万(册印)起,他是在这个国家每本书都保持这个印量的纯文学的唯一一人,这个标准在任何社会都是主流作家,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一直受到读者喜欢和追捧的作家。王安忆的印数比贾平凹要小很多,但王安忆的每一本书都会有大量的报道,一本书出来就会被热评、热议。
书乡周刊:那么除去销量和业内的评论,你怎么评价自己在文学史的位置?
马原:我肯定是这个时代写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这个我不用谦虚。我写了四十多年,到现在还有人看我的书,我四十年前写的小说,现在拿出来还可以出版。我其实很为我不是一个主流作家而骄傲,我的小说不过时。在我的《牛鬼蛇神》里可以把三十年前的小说拿过来塞到里面,大家看的时候觉得无缝对接,只有那些好事的人会说,马原的小说里有七个他之前的小说。
书乡周刊:《黄棠一家》也有评论说写的事件是许多新闻事件的集合。
马原:他们说我写的是新闻串烧,连这个话都说得出来,这是我五年前写的啊。其实我想说,你看到小说里面的那些事件,我在五年前就看到端倪了,你们觉得像新闻,但是再新都是五年前的。因为我不必去跟媒体打口水仗,去支人家的罗锅。但是大家说我写新闻串烧的时候,倒不如说是旧闻串烧,准确说是我对我们时代出现的乱象的一种编织。
书乡周刊:“黄棠一家”的意思谐音就是“荒唐一家”,所以你要表达的价值观其实很隐晦。
马原:我要表达我们现在的拜金、物质、功利……真是糟糕,我把它们编织到一个家庭故事里,写了这样一家人。我跟鲁迅那种批判还不是一回事,他是带着针砭、摧毁、作战的意味,我根本不是。但我写这一家人做的事儿不都冠冕堂皇吗?黄棠做了坏事了吗?黄棠的儿子做错了吗?也不算错。但是整个(读)下来你会觉得这家人这么可笑。
书乡周刊:所以你刻意把这一家人的结局写得不好?
马原:其实不是刻意的,你说是悲剧也好,闹剧也好,我是先知道结尾,再去写前面的。这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尾,这个结尾是这个家庭的支柱。中国很多北方城市都缺水,这个家庭和所在的城市其实是很多北方城市的缩影。我当时想的其实不太多,更多的是一个小说家一辈子的直觉和经验。我有一篇文章就叫《金钱是个什么鸟》。
书乡周刊:小说里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作家把自己写进去了,故事结尾,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望黄棠,这个朋友叫马原,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叫马原,他是个小说家。他也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样设计有什么意味?
马原:我一直觉得写书的那个人一直是在场的。他隐身也罢,不隐身也罢,我就是要用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论去告诉读者,我在,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身边,他在看你们,在看你们的故事。因为小说的方法论里面最重要的是视角,最主要的是上帝视角、全知视角和主观视角,其实还有第三种视角。我们知道人物关系有三种,我、你、他,这三种视角在小说里我都用过,当然现在我写了几十年小说已经不太耐烦去不停地转换视角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告诉我的读者,写书的那个人一直都在,有时候你们没发现他。这是一个很大小说的奥秘。小说视角永远是小说家最有趣也最丰富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