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琼:痛苦和喜悦都在诉说中清晰 ——关于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新作《一匹马走进酒吧》
来源:文汇报 | 张琼 2018年03月23日0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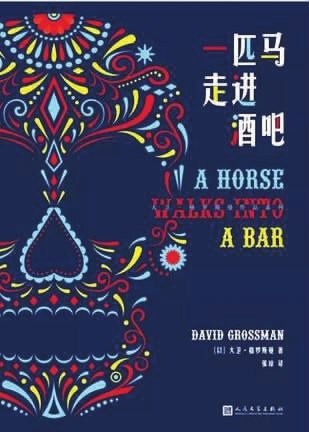
这部作品以奇幻独特的叙述结构,通过一个过气喜剧演员在酒吧的一次夜场单口相声表演,讲述一段交织个人、家庭、民族的悲喜剧,痛苦和欣悦都在诉说中清晰。
《一匹马走进酒吧》,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给小说起的这个匠心独具的标题让人纠结,其实,那匹马是被他一带而过的,读者稍不留意就会忽略。“一匹马走进酒吧”,这个表述来自书中的一位军用卡车司机。他受命负责将当时在营地军训的少年杜瓦雷送往耶路撒冷参加葬礼,但是整个过程中,司机和杜瓦雷都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究竟是谁去世了。他们自觉巨大的悲伤即将降临,可是一切尚未水落石出。于是好心的司机编织了不少荒诞的谎言和笑话一路哄骗杜瓦雷:“一匹马走进了一家酒吧,问酒吧招待要了一杯啤酒。招待就给他倒了一品脱,马喝完酒,又要了威士忌,再喝完,它说要龙舌兰,然后又喝了。它再喝伏特加,接着是啤酒……”
这是全书唯一与书名相关的叙述,前后的相关性甚少,只留给我们无限延宕的反思。这匹进入了酒吧的马就像赶赴葬礼途中的笑话一般,不合时宜,十分怪异尴尬,也像小说本身一样,看似是整场喜剧表演,实质在笑声的反衬中让人类的悲剧更显现其悲恸的本质。这匹马也是杜瓦雷的隐喻,经历了各种生活悲剧的他却要从事喜剧演员的事业,在引发他人爆笑和喜悦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若说全书中还有一处与马匹略有关联的,就是少年杜瓦雷的瑰丽奇幻想象。在幻想中逃避现实痛苦的杜瓦雷爱上了用手倒立行走,以此“拯救我自己”,可是在父亲的责骂和纠正下,他不得不用脚走路。某日杜瓦雷突发奇想,想到了象棋棋盘,于是他故意一会儿走对角线的象步,一会儿走直线的车步,一会儿走马步,并自觉通过这种游戏式的想象,假设周围的人们都在与他玩象棋,而人们居然不自觉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整条街都成了他的棋盘……他也由此精神胜利地逃避了被周围孩子欺凌的困境。
这样的游戏思维,也许就是创伤后得以生存的策略,也是作家所要揭示的普遍隐喻:人类分担着同样的历史文化记忆,而一旦体验了马走进酒吧的尴尬错位,就像面对生存境遇中的错愕和格格不入,生发出境由心生、艺术永恒的深意。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一次马匹走入酒吧的冒险:人们会做出何种反应? 如此大胆的尝试是否令人震惊? 震惊之后又会有什么? 是否虚构和魔幻比现实更为真实?
我的情绪始终被作家巧妙嵌入的悬念推动,小说的几百页叙述只是短短的一个单口相声表演,其中具体到每个细节的表演叙述,看似冗长,其实跌宕起伏,戏剧反讽,喜剧的表象下蕴藏着本质的悲痛,心理创伤和集体无意识渗透在字里行间,令人叹为观止。
格罗斯曼出生并生活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创作了多部畅销小说、非虚构作品,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布克奖的评委们一致认为“他的作品是极具吸引力的沉思录,展现了即使在最为黑暗的时刻,我们如何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羔羊的微笑》 揭示1967年巴以冲突的六日战争中的道德和存在困惑,1986年的 《证之于:爱》充分展现了极具创新意义的写作才华,被认为是开创了以色列的魔幻现实主义。他引领读者以文学想象的形式亲历现场,小说的四个部分以截然不同的风格,贯穿意识流、自然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组合成为后现代文学创作、创伤批评、幽灵批评的典型研究案例。
格罗斯曼其它的长篇作品,如《锯齿形的孩子》 《决斗》 《亲密文法之书》 《做我的刀》 等,都有着独特奇幻的创作风格,密切关注以色列的现实生活及犹太人的生存命运。他笔下的母亲历来受到关注,因为以色列犹太母亲形象就像生活在战乱和创伤危机中的民族隐喻。有学者曾言:“以色列犹太母亲,以及母亲的文化身份带有悖反的矛盾因素:一方面她们意味着亲密、养育、关爱、谦卑和宠溺;另一方面她们又必须为捍卫民族而武装自我。”小说中杜瓦雷的母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身心带有创伤烙印,可她又是儿子真正的灵魂慰藉者,能宽容接受甚至欣赏儿子所有的奇思幻想和乖戾。然而,在她的家庭和社会的角色调整中,母亲不堪重负,最终唯有抹杀自我的存在来解决这一格格不入的痛苦。她的尴尬和不适,也像一匹马走进酒吧般荒诞不堪。无论在场或缺席,母亲给儿子带来了深远重大的影响。
在阅读中,我一直感受着作家所言的创作小说的至高喜悦,即在叙述过程中生命的完整性。这种创作的喜悦同样适用于作家笔下说单口相声维持生计的杜瓦雷。口述渐入佳境,痛感和快感并存,表演者起初和间或的讨好观众最终让位于发乎本能的诉说之瘾,痛苦和欣悦都在诉说中越发清晰鲜明。
格罗斯曼曾经在访谈中坦言:“最能捕获和吸引我的主题就是个人和无常的外部事件之间的冲突,个体能够在无常面前补偿和重新定义自我。对于我而言,每一部作品就是一部分答案。”由此看,我们应该释然他作品中看似离题散乱的思绪和话题,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这些偶发而散漫的元素与个体生命产生碰撞冲突,从而来寻求补偿和答案。这场延绵不断的叙述,穿插着观众的各种诸如不适、愤怒、失望、放弃、期待、同情等反应,也交织混响了作家所能预见的所有解读回应,其中藏着作家的潜台词:好也罢,坏也罢,悲也好,喜也好,我们就是这样用话语来表达自我,尤其是深入意识的痛苦和回忆,这是我们经受磨难的方式,赎回失落的途径,也是我们有勇气再次回到现实的力量。小说中的观众“我”就在这一晚经历了记忆被叙述唤回,麻木灵魂逐渐觉醒的过程。
人们害怕将希望和信任寄托在任何他人身上———这种难以言说的苦痛贯穿整场脱口秀,在这样的徒劳绝望中,杜瓦雷通过喜剧表演做出的不妥协姿态令人动容,他的唐吉诃德式斗争仿佛在悄然融化坚冰,捍卫着人性光芒战胜仇恨。因此,在他的叙述中,那些不断用荒诞方式缓解痛苦和绝望的人们,最终会让观众和读者在笑声中流泪感动,在曲终人散时有勇气面对当下和未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一匹马走进酒吧》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