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德国文学:辨认自己和理解时代
来源:文艺报 | 钦文 2018年02月12日10:00

丹尼尔·凯尔曼

罗伯特·梅纳瑟

娜塔莎·沃丁

林小发

扬·瓦格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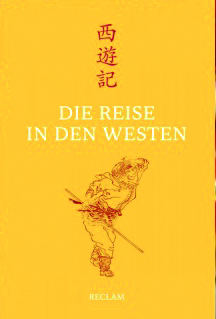
德译本《西游记》
阅读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躲避当下,我们可以从书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而后代也会从中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说起2017年的德国文坛,就作品而言,似乎是个小年。评论界和读者公认的优秀作品不多,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新人涌现,多少有些令人扫兴。
虚构/非虚构:历史之镜映照现实
书在一本本出,也总有读者去买、去读。据统计,去年排在德国图书销量榜首的是挪威小说家马娅·伦德(Maja Lunde)的处女作《蜜蜂史》,居然将老牌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最新作品《起源》甩在身后。《蜜蜂史》借着虚构的故事来反映全球生态危机,正好迎合了德国人一向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英语里有个词German Angst,可译作“德式焦虑”,意为即便是过着“好日子”,也总是怕这怕那,忧心忡忡。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不出所料地畅销德国,与此也大有关联。销量榜单前列总有半数左右是引进图书,这在德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就阅读而言,德国读者是非常“国际化”的。
文学图书榜上,最热销的德语原创作品是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的《蒂尔》(Tyll)。说起这位作家,喜爱德语文学的中国读者不会太陌生,其成名作《丈量世界》也在中国获得不错的反响,迄今已有两个译本。书名“蒂尔”取自家喻户晓的德国民间故事人物蒂尔·欧伦施皮格尔(Tyll Ulenspiegel),这位来自乡下的年轻人最擅长恶作剧,专门捉弄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凯尔曼将原型蒂尔“借调”到200年后的时空中,把故事情节放在三十年战争的大背景下。蒂尔在德国各地流浪,所到之处不拨弄出点“是非”绝不善罢甘休。小说里,善于治病救人的父亲被当作巫师处决了,蒂尔不得不逃亡,临走还拐带上了面包师傅家的闺女。凭着能言善辩、诡计多端,他成了流亡中的波西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五世宫廷中的弄臣,由此成为这场战争中许多历史事件的“目击者”,跟随着一个个真实或虚构的大小人物亲历了三十年战争,期间也曾命悬一线,但强大的求生欲望让他一次次起死回生。对于熟悉欧洲文学传统的人而言,这部小说就是盛在“愚人文学”和“流浪汉小说”旧瓶里的新酒。相似的战争题材,很容易让人想起《痴儿西木传》和《好兵帅克》。这部作品延续了《丈量世界》的手法,完美地将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结合在一起。作为民间故事书的《蒂尔·欧伦施皮格尔故事集》是轻松愉快的,但小说《蒂尔》里的许多情节读来却让人压抑,战争的残酷体现在书中故事里,作家写下这些不再是为了娱乐读者,他让读者无时无刻不陷入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之中。
今年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400周年纪念,德国多家出版社提前推出了这一题材的作品,《蒂尔》无疑是虚构类中的佳作。在非虚构类中,德国当下最著名的政治学者明克勒的《三十年战争——欧洲的灾难、德国的梦魇》最受人关注,批评家们对这部近千页的作品不吝赞美,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对三十年战争研究最为透彻的历史著作。对于当下危机四伏的欧洲而言,该书也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人们总担心厚重的作品越来越不受欢迎,然而德国近几年颇有一些篇幅在千页上下的长篇巨制,非虚构类作品中就有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温克勒的《西方的历史》、马图斯的《启蒙运动》、波尔希迈耶尔的《何为德意志》,它们都进入畅销书行列,不禁令人称奇。据悉,《三十年战争》一书已被国内某出版机构购得版权,对于国内读者而言,无疑是个福音。
对纪念日的关注,是德国出版界的惯例。一般而言,出版商和作者会在许多年前就约定写作计划,以便图书可以如期出版。过去的一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在发源地之一的德国,2017年被称之为“路德年”,围绕宗教改革的纪念活动多到连许多文化和媒体界人士都觉得“不胜其烦”。自2016年起,有关宗教改革和马丁·路德的图书就扎堆问世,既有新书,也有再版。当今欧洲仍是世俗化占据主流,但面临着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纪念年里的众多宗教、文化、艺术活动,外加图书,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宗教和信仰的契机。
文学奖:辨认自己的模样
图书奖总是人们的焦点,只要进入候选的长短名单,图书的受关注度就会大大提高,更不用说最终的获奖作品了。2017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图书奖授予了讽刺小说《首都》(Die Hauptstadt),作者是年逾花甲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Robert Menasse)。小说中故事的主要场景在布鲁塞尔——欧盟的“首都”所在地。为了筹备50周年庆典,一位主管文化事务、来自希腊的欧盟高官委托一位奥地利籍的专员策划一个活动,旨在改善欧盟日益不佳的形象。这个奥地利人突发奇想,提议让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活动代言人。一心想高升的希腊人同意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想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来自上上下下的重重阻力甚至是阴谋,计划最终流产。作家为了创作此书,特意在布鲁塞尔租房,居住在“现场”。他不仅在观察,而且还经常出初入欧盟各机构调研,与当事人(官员、政客、学者)交谈,与很多置身现场之外的欧洲人一样,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弄明白一个问题:欧盟究竟在干什么?小说一开场便跳出一幅充满隐喻的画面: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只猪在街头奔跑。在作者看来,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生活现象都可以用猪来隐喻。围绕着猪的养殖、屠宰、出口,欧盟官僚体系的繁复和成员各国的同床异梦都得以生动地展现。
在着手创作小说之前,梅纳瑟就频频出席各类论坛和讲座,在公共空间里探讨欧洲问题,演讲和文章于2012年结集出版,取名为《欧洲快报》,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德国19世纪作家毕希纳的《黑森快报》。的确,内中观点鲜明、语言辛辣的文章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当然也引起激烈争论。较之于此,《首都》是用文学思考欧洲的一种尝试,被批评家称为欧洲第一部“欧盟小说”。图书奖评委会认为,作家“用文学手段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当代人,他们可以在这部作品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而后代也会从中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虽然作家对欧盟的体制和运作颇有微词,但切莫将小说视作反欧洲的作品,梅纳瑟在获奖答谢辞里揶揄欧盟机构“有时滑稽固执”,但有时候也显得“非常果敢”。对于欧洲统一,他坚信,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进程”。支持欧洲统一的人不会忘记他于2013年与政治学家乌尔里克·圭罗联名发表的《建立欧洲共和国宣言》。联想起前一年难民题材小说《遭遇》的获奖,不难看出评委们的旨趣。在面临种种现实问题的欧洲,人们不仅期待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也希望能够从文学艺术中找寻灵感。
春季的莱比锡书展是读者的盛会,莱比锡图书博览会图书奖的角逐也十分激烈。文学组的最终获奖作品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Sie kam aus Mariupol),这是一部“含有虚构元素的传记”,取材于作者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母亲的悲惨经历。一次百无聊赖的网上搜索开启了作家对母亲身世的探寻,借助各种线索和信息,业已模糊的记忆在眼前铺开。母亲叶夫根尼娅出生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个上层家庭,书中前半段讲述了家族在20世纪初的种种经历。二战后期苏军反攻,曾在德国占领机构工作的母亲跟随大自己20岁的丈夫尼古拉来到德国,落脚在莱比锡的一座强制劳工营,作为劳工受尽屈辱。1945年,父母逃往巴伐利亚。但仍然被视为异类,又被安置在一个“流人营”(Displaced persons camp)里,等待被遣送回苏联,只是由于程序上的错误,他们免于被遣返。作者娜塔莎就是在这一年底降生在纽伦堡郊区一个五金厂区的小棚户里。这对来自外乡的人在战后的德国毫无生存机会,在贫困、饥饿、屈辱、隔绝中,父亲酗酒,埋头阅读俄语书;母亲日渐疯癫,直到1956年的一天自尽而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家长久以来不知道父母是强制劳工,没有人告诉她,无论是父母还是周遭的人。对于百废待兴的德国而言,强制劳工似乎被彻底遗忘了。战争结束了,“在德国,一切都要变成新的,房子、家具、人,这是一个重生的时代、遗忘的时代”。留在她幼小记忆中的是,她这样的孩子在别人的眼中不过是“战争遗留下来的渣滓”罢了。该书再次揭开了德国历史上的一块伤疤。二战期间,在德国土地上共有几万个战俘、劳改、集中营。据著名历史学家赫尔贝特推测,二战结束时从这些地方释放出来的战俘、劳工和集中营囚犯共计八百万到一千万人,作家那“可怜的、弱小的、疯癫了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幸存者”。在写作过程中,娜塔莎·沃丁在搜寻素材时发现,她在乌克兰的收获居然比在德国的收获大。许多档案材料被刻意销毁,记忆随着当事人的去世而荡然无存,即便尚有知情人在世也大多缄口不言。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德国人开始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反思。对于迫害、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大部分民众已有所认知。然而提起战俘营、劳工营里发生的悲剧,人们几乎一无所知。据统计,《她来自马里乌波尔》自2017年2月问世后已加印多次,成为德国当年最畅销的文学书之一。相信随着该书的传播,这段被遮蔽和遗忘的历史会重新进入公共记忆之中。
说到莱比锡书展奖,值得一提的当然是翻译类图书奖的归属。获奖作品是林小发(Eva Lüdi Kong)的《西游记》德译本,这是史上首部德文全译本。有关译者和这个译本,去年中文媒体多有报道,此不赘述。此外,一年一度的“世界最美图书奖”也是书展的亮点之一,来自中国的两部作品获奖,分别是朱嬴椿设计的《虫子书》(银奖)和周晨设计的《冷冰川墨刻》(荣誉奖)。
在德国,一年一度最受关注的文学奖莫过于格奥尔格·毕希纳奖。此奖不针对某部作品,而是对某个作家整体创作的肯定,获奖者相当于进入当代德国文学的名人堂,成为活着的“不朽者”。2017年获此殊荣的是一位诗人,扬·瓦格纳(Jan Wagner)。在历届获奖者中,小说家居多,诗人是少数。瓦格纳1971年生于汉堡,如同当代的许多德国作家一样,科班出身,曾在汉堡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柏林洪堡大学修习英美文学。2001年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天上的钻探实验》(Probebohrungen im Himmel),迄今为止发表了11部诗集。评委会认为他的诗歌“在与伟大诗歌传统的对话中诞生”,“既有充满游戏意味的语言之乐,又有超凡的形式把握能力,兼具音乐的感性和智性的明快”,对于诗歌而言,这样的评价几乎是无以复加了。
瓦格纳创作的特点之一,在于善于书写世间常为人所忽视的微小事物,例如收录在《十八个馅饼》中的这首诗:
蘑菇
在林中一片空地上,我们遇到它们——
穿行于黄昏的两支探险队,
彼此静默注视,充满紧张——
一群蚊虫发出电报嗡鸣。
我奶奶因蘑菇馅饼
而闻名。食谱锁进了
墓地。凡是好东西,她说,
填充你不多于它自己。
后来在厨房,我们把蘑菇
举到耳边,转动蘑菇柄,
等待里面细微的咔哒声——
那准确的密码组合。
(明迪 译)
正如他在颁奖典礼答谢辞中所说:“我写诗源自一个信念:极微小之事物也能成为诗。有眼有耳,(就能感受到)一首诗中蕴含着一些极复杂的东西,它们能够让人直接而感性地体验到美丽和晦暗。诗歌不是要与这个世界和当下背道而驰,虽然它避开那些热门的话题。我坚信,只要用尽一切语言上的可能性,无论诗歌以狗窝还是历史人物开篇,那都无所谓,因为一首成功的诗歌会邀你重新看世界、重新思考,它让你无法拒绝。”
除了写诗、主编诗集外,瓦格纳还乐于从事诗歌翻译,对于他而言,翻译也是创作。说来也巧,就在获奖公布之后,他和其他几位德语诗人一同来中国参加德国歌德学院主办的“诗人译诗人”系列活动。在南京有一场工作坊,他与本地诗人朱朱合作,相互翻译对方的诗歌。互不通对方语言的诗人,在专业译员的帮助下,尽力体会对方诗歌的内容和意蕴,试探、揣摩、猜测、理解。一首诗歌的翻译耗去整整一天,次日上台朗诵时,仍觉不满意。作为旁观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瓦格纳所说的“翻译即创作”。席间,我问其获奖的感受,诗人坦言很开心,认为这对于当代德国诗歌的创作和阅读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广。
文学、出版体现这个时代
德国的文学奖多到眼花缭乱,除了圈内人和少数文学爱好者,谁得什么奖未必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很多奖项更像是资助金——那些处于起步阶段、已经通过作品展现出实力的作家凭借这些奖金可以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度过一段安心创作的时光。在众多此类奖项中,沙米索奖颇为特别。该奖创办于1985年,是以德国浪漫派著名作家、用德语创作的法裔作家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的名字命名,旨在奖励非母语作家用德语创作发表的优秀作品,此外副奖也资助尚未发表的优秀作品,每隔几年也会向某位作家颁发终身成就奖。2007年,旅德华人作家罗令源曾获该奖资助。历届获奖者中,已有人跻身一线作家行列,如土耳其裔作家菲利顿·宰莫格鲁和匈牙利裔作家伊利亚·特罗亚诺夫。
之所以要介绍该奖,只因为2017年3月该奖项最后一次颁发,主办方博世基金会终止了这一持续了30多年的项目。2016年,停办消息一经刊出,有识之士为之叹息。移民融合问题持续困扰德国,这一奖项的存在和获奖者们无疑是对这一问题的某种积极答复。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特约评论中,特罗亚诺夫对该奖的停办表示震惊,认为尤其是选错了时间:“百万难民进入德国,他们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会给德国人带来闻所未闻的故事、体验、书写方式,在这样的进程中,沙米索奖是一个绝佳的平台。有关该奖是否有必要的讨论由来已久,批评者(也包括作家)认为,这个奖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获奖者边缘人的角色定位,与其说促进融合,倒不如说强调了归属困境。对于特罗亚诺夫提出的新移民文学前景,博世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的答复是,“这样的文学还不存在,待其形成尚需时日,到了那一天,人们自会找到新的途径去扶助它”。
无论如何,最后一位获奖者阿巴斯·基德尔(Abbas Khider)还是值得祝贺。他在萨达姆统治期间多次入狱,释放后在中东多国流亡,2000年来到德国申请避难,之后在慕尼黑和波茨坦修读文学和哲学。他将德语视作新的家园,以此与自身的经历保持距离。一方面他将“逃亡、流亡、人的毁灭”视为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他又避免书写个人的苦难,更试图在作品中将惨痛转化为欢快。在颁奖典礼上,2011年度的毕希纳奖获得者德里乌斯在致辞中如此评价这位来自伊拉克的作家:“阿巴斯·基德尔获奖当之无愧,不仅是因为他让我们直面德国式的虚伪。他的小说富有诗意,构造精巧。他让我们微笑,玩弄着那些陈词滥调,让我们惊讶于困境中的奇迹。”
2017年9月底,德国议会选举结束,组阁谈判延宕至今,新政府迟迟未能产生。相对于无所作为的看守政府,在不能确定是否重新大选的情况下,新一届的联邦议会已经开始运作。在本次大选中异军突起的选择党(AfD)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派,打乱了德国的党派政治格局。德国的民意在向右转吗?几年前,社会民主党政客萨拉金写了一本《德国在自取灭亡》讨论德国当下现实问题,其中涉及德国移民问题,尤其提出穆斯林背景移民的人口增长对德国未来会带来严重威胁。此书问世不久便成了畅销书,其“成功”颇能反映德国民众的心态,这也引起了公共领域内的热议。意见主流对此书持否定态度,社民党也逼迫萨拉金退党。时隔几年,又有一本书的出版激起了类似的争议。
《日耳曼的末日》是已故德国历史学家希弗勒的遗稿结集,由新右翼的安泰俄斯出版社于2017年2月推出。据出版方称,此书起印20000册,可见信心十足。此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的标题成了书名,全书收录了30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充满修正史学的味道,以阴谋论的腔调判断史实,这一姿态与德国战后主流的反思史学背道而驰。其实书中的许多观点并不新鲜,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论战”中,右翼历史学家一派就坚持类似立场。《日耳曼的末日》的畅销得益于《明镜》周刊记者萨尔茨维德尔的推荐。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类作品排行榜的荐书人,在6月榜单的遴选中,他将自己手中的所有分值全押在了这一本书上,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帮助该书登上了月度最佳书榜的第九位并自此大卖。之后几个月,在亚马逊德国的非虚构类图书热销榜上,《日耳曼的末日》数度登顶。此书也一度出现在《明镜》周刊的图书排行榜上,然而不久后便消失了。在答复读者质疑时,编辑部称,此书若无萨尔茨维德尔的推荐断不会有如此影响,出于避嫌,还是让它下榜为妥。此举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非议,认为这是对公众的欺骗。
媒体热议之后,历史学家也纷纷站队表态。支持一方认为,虽然此书在论证和细节上有纰漏(毕竟是未经审定的遗稿),但细读之后还是能发现不少真知灼见的,只匆匆一瞥便对此书妄加评判是不恰当之举。反对方则认为,书中充斥着反犹主义倾向,拒绝承认德国战后对反思历史的成果。总体而言,媒体和学界的主流对此书持否定态度。但普通读者的反应却耐人寻味,以亚马逊读者留言为例,八成以上的人给了五星好评。
且不论孰是孰非,从这一“事件”中获益最大的是出版商。安泰俄斯出版社借此东风,踌躇满志地出现在去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之上。在一场围绕新书《与左派相处》的讨论会上,左翼人士与右翼人群发生言语交锋,并相互推搡。而在此前一天,一位听众用拳头袭击了一家左翼出版社的出版人,导致其受伤并入院治疗。这种直接冲突,在过往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极为罕见,德国社会的左右意识形态分裂日盛可见一斑。
限于篇幅和精力,2017年德国文坛还有一些书、人、事无法在此一一交代。其实过些时候,还能记住几个人、几件事?最终能留下的无非还是几本值得去读的书罢了。套用前文中不同出处的两句话来结束这篇年度总结吧:阅读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躲避当下,我们可以从书中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而后代也会从中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