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点燃甲马纸 我就成了时间旅行者
来源:晶报 | 伍岭 2018年01月16日08:05


默音作品四种 《甲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姨婆的春夏秋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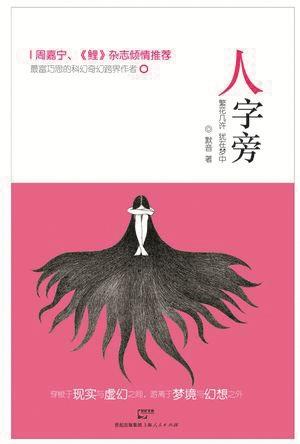
《人字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月光花》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说起默音,或许不少读者会有些陌生。《甲马》书上对她的介绍是这样写的:作家、翻译家。1980年代生于云南,后迁居上海。写科幻小说出道,近年来创作多混合了现实与奇幻。在出版的小说中,《姨婆的春夏秋冬》获上海作协2015年度优秀长篇。除此之外,默音还翻译了多部日本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并长期撰写与日本文学、文化相关的文章。但这只是你认识默音的维度之一,要了解一名作家,最重要的还是阅读其作品。
《甲马》历时八年完成,其间一共修改了四稿,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渐渐写成了由三个故事串成的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家族的悲喜。默音用文字雕刻的不仅仅是父辈们的一生,更是年轻一代逐渐漠视的家族历史。尽管有宏大的视野和企图,默音依然将笔触落在了人物和记忆当中,成长的困境和无法倾诉的过往都在她的笔下“燃烧”,穿过曾经的硝烟和城市烟花,皆能找到自己的存在和父辈们的艰辛。
默音现已迁居上海,除了写作和翻译,她还从事图书编辑的工作。尽管她的多部作品都设置在家乡云南,但其实默音的文学梦与深圳也大有渊源,甚至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月光花》都有以深圳为背景的描写。记者对默音的专访,谈到了她在深圳的生活与学习,也谈到了她的作家成长之路。
深圳是悬浮在我经历之中的一段记忆
晶报:可以说你的文学梦起步于深圳吗?
默音:我确实是怀揣着文学梦去的深圳,这得从头说起。我念书比较早,17岁从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商场里当营业员,后来辞职去念了计算机专业的大专自考,再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已是千禧年的春末了,那时20岁还不到,却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后来进了一家日企做翻译,顺便管理办公室的文档,应该算是个“杂役”(笑)。之后转到同一个公司的研发中心担任系统工程师,多少算是专业对口了。坦白说,选择学计算机和自己的兴趣并不相符。所以,一心想从事文字工作的我逃离了那个地方,便在2004年来了深圳,最终在一家日文杂志社落了脚。在深圳生活的几年是超负荷的,也是我的日语进步最快的时光。后来能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念研究生,和这段时期的努力密不可分。
晶报:你如何看待深圳这座城市,它对你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默音:在深圳的几年对我来说有些特殊,学到的东西很多,认识的朋友却很少。所以就导致这段时期像是悬浮在经历中的记忆。我现在也还记得坐公交车从滨海大道经过时的那种欢畅,因为那个时候车开得很快,却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欣赏。其实这样的街景和这样的速度,在其它城市是看不到也经历不到的。在深圳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把写的爱情故事贴在自己博客上。
我学计算机一方面是父母对就业的考虑,一方面也是“想纠正自己的文科气质”。后来发现这是多此一举,文科气质这种东西很难被改变,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还是会想要写作。在深圳的这段时间比较宝贵的经验应该是四处走了走,行走在大街小巷里,看到了一些特别有生活气息的地方。2012年我写出的长篇小说《月光花》就有很多场景是深圳的,包括对“城中村”的描写,都来源于那个时期的观察。
晶报:朋友少,那你在深圳是如何度过文化生活的?
默音:在深圳工作期间会去香港买书和看影展,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和一些二楼书店,都是我常去的地方。那个时候的阅读口味还很单薄,我记得买的主要是设计类书籍和一些生活随笔,例如欧阳应霁的书。要说和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大概算是在香港的Page One书店看到码堆的“The Kite Runner”(《追风筝的人》),就买回来看。那是我完整阅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完全没想到后来它的中译本会是那样畅销的一本书。可能因为做杂志,周围一起玩的年轻人也有设计师,看展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2005年在深圳看“大声展”的感觉是非常新鲜和独特的,后来在上海看更有名的国际性展览,也很难再现那种感触。
我回看了自己在豆瓣标记的第一本书是黄碧云的《后殖民志》(2007年),这本书应该是在深圳期间买的,也说明了深圳-香港这条轴线给我的一些影响。现在公众号传播更快,经常看你们《深港书评》推送的文章,感觉今日的深圳比我记忆中的在文学上要鲜活得多。大概是从前我忙于工作,并没有去探索可能存在的文学环境。虽然我不认为有所谓的“文学圈”,创作者毕竟都是各自默默努力着,但那个时候确实有种年轻的茫然,可能是因为没有遇到同道中人吧。
“甲马”让我连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
晶报:你的新书《甲马》,提及了云南谢家可利用燃烧“甲马纸”看到别人记忆的故事,能说一说“甲马纸”是张什么纸吗?
默音:甲马是一种刻有神像的木板,甲马纸就是用这种刻板拓印的版画。云南人在清明、中元节和春节等节日燃烧甲马纸,用来祈福消灾。在云南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妈妈是上海知青,并没有机会看到甲马纸,我第一次“发现”的甲马纸,好像是在鲁迅收藏的版画里看到的。《甲马》出版后,我在豆瓣贴了一个解说甲马的科普贴,没想到很多人回复,我也才知道河南和西北都有类似的东西。
晶报:你为了写这本书,还特意回云南拜访了刻“甲马纸”的大师,能说说这段经历吗?
默音:大理上关的张瑞龙师傅是《甲马》封面所用甲马的制作者,出版社专程向他取得了授权。我想我不能像叶公好龙一样,写了关于“甲马”的小说,却没亲眼见过甲马纸的制作过程,所以趁着某次假期回了趟云南,专程去拜访他。去了才发现甲马纸已经很出名了(笑),张瑞龙师傅如今是非遗传承人,开了个甲马传习所,有很多学生乃至国内外的团体到他那儿体验甲马纸的制作。我也试了。实际看到书里的甲马纸在不到一分钟就被拓印出来,感觉很神奇。
晶报: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写一本和“甲马”有关的故事?
默音:写作者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比较便捷的方法是写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果要写历史,就会面临一些难度,首先是没有实际经历打底。当然不是说写当下就比写历史容易,想要写好,都很难。重点在于,当历史落到小说里,你要选择怎样的一个叙述角度。
《甲马》里有一些非常小的细节是我听当过知青的母亲讲的,例如偷玉米怕被人发现,举着玉米蹲着,装成是一株玉米的故事。我母亲讲知青时代的事不太多,也因此,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总是置身于历史潮流中,但每个人经历的都是些个别的小事。可能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些很个人化的小事吧,写一个家庭在时代中的离合,只是写着写着,我发现势必要写主人公周围的人,故事也变得不那么“小”了,而“甲马”的出现正好连接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关系。
晶报:《甲马》经时八年完成,这期间你做了怎样的改变?
默音:完全没想到会花这么长时间。不算中间的零碎修改,一共写了四稿。第一稿就像之前说的,只是写一个“找妈妈”的故事,时间线全部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2008年写的时候,对我来说也就是十年前的故事,不算太远。到了现在,离这个故事的时间线都快二十年了。《甲马》写了八年,当然不是指八年时间里一直在写,中间也停下写过别的小说。可能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重量需要这么久的寻找和积累吧,到了大家现在看到的第四稿,它长成了一个三十万字、有三条时间线的故事。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三个小说的嵌套。
晶报:《甲马》故事以一段段记忆为线索,却必须通过燃烧来找寻,记忆这种东西是否就像甲马纸中的“虚空过往”那般有所暗示?
默音:我最近在读人工智能的书,读到一个有趣的理论,那就是,我们相信记忆是“客观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比记忆更主观的存在了,这里指的是概念上的记忆——譬如桌上有个苹果,人们不用一直盯着看也知道苹果在那儿。这就是关于“桌上有个苹果”的记忆。我们脑海中的记忆就是这许许多多的“客观事物”的叠加。强烈的记忆会感觉就像发生在最近,而模糊的记忆则好像是久远的,大家以为是呈时间序列排列的记忆,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人们不仅以为记忆是客观的,还认为记忆是线性的。我们所拥有的记忆,就构成了我们自身。
《甲马》中的“甲马纸”是类似计算机bug的存在,把别人的记忆纳入自己的脑海,这是一个消解了过去和现在,也消解了自身和他人边界的举动,点燃甲马纸,谢家人就短暂地成为时间的旅行者。小说作者其实也像一个烧甲马纸的人,靠的是不断的思索和探究,在文字里成为别人。
翻译与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晶报:除了《甲马》,你对自己的哪些作品比较满意?
默音:《月光花》因为出版比较早,感觉不够成熟。从《人字旁》起都算是相对满意的了。《姨婆的春夏秋冬》由四个中篇构成一个完整的长篇,我在其中学到了很多,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写“过去的时代”,感觉比想象中容易。查资料当然是不可少的,写作的时候要忘掉自己看过的东西,随着感觉走,不然很容易变成资料的堆积。
晶报:你觉得一本好的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默音:好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场”。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气质,具有“场”的小说,能把读者带到未知之境,读完后或多或少总能感觉到一些心境上的变化。
晶报:能说说你喜欢的作家吗,他们对你又产生过哪些影响?
默音:首先喜欢的是日本作家。我读得最多的是村上春树,少时看译本,最近十年则是读原文。其他的日本作家就看得没那么全了,读得多一些的有角田光代、三浦紫苑、吉田修一、米原万里、梨木香步、高村薰等。欧美作家里我喜欢厄休拉·勒古恩、约翰·欧文、萨拉·沃特斯和科伦·麦凯恩……中国作家看得比较零碎,反复读的只有金庸、王小波和路内等几位。但如果说对我有影响的作家,约翰·欧文算一个吧。欧文是喜欢写长篇家族故事的作家,也是老派的注重故事性的(狄更斯式)作家,我在他的笔法里学到了很多。
晶报:你翻译和编辑了哪些日本作品?你觉得翻译、编辑和写作有必然的联系吗?
默音:因为有三年时间是自由译者(同时也在创作小说),这时间翻译了不少作品。自己比较认可的有《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家守绮谭》《雪的练习生》
《摩登时代》等,还翻译过一位哲学家写京都的非虚构作品《京都人生》。
我的编辑工作是从2012年开始的,比较开心的是亲手把三浦紫苑“真幌站前”三部曲做了完整的引进,修订了译文,并请了可靠的译者李建云翻译了后两册。让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曾为日本作家吉田修一担任过图书编辑,这些经历都让我受益良多。从翻译到编辑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编辑工作虽然比翻译要复杂得多,涉及很多细节,但如果没有翻译能力打底,做外国文学编辑想必是很吃力的。个人觉得这两项工作看起来都与写作的关系不大,但它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晶报:你这么关注日本作家,对于日本文学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看法?
默音:说日本文学这个概念是有点大的,不如来看看中国引进日本文学的情况。个人感觉国内的日本文学译介是相当热的,大部分在日本销量好的作者都有引进,偶尔还是十分具有文学性但销量一般的,也获得了被译介的机会,例如我翻译过的多和田叶子(她用日语和德语写作)。日本作家整体上都非常勤奋和纯粹,基本上我关注的那些作家,大概除了以精雕细琢著称的高村薰外,都能看到他们每年有新书出版。虽然这些人的作品无法保证每本都能维持在同一水准,但就我个人而言,能持续关注一些作家的作品也是很有意思的。
晶报:持续关注某些作家之意义,对你来说是否对写作有更多帮助?创作上会少走弯路吗?
默音:我这是纯粹的粉丝心态,爱一个作家就希望像读编年史式地读他/她的书,当然实际阅读的时候很少真正按创作顺序来读。至少阅读村上春树的体验就是,隔几年重读又会有不同的发现。有时候读了他在某部小说创作期间写的杂文,对其作品背后的理念多少也会有所察觉。读他的作品并不是由A到B那样直接,而是有可能你在杂文看到A,小说呈现的是C,还有一个只有作者本人知道的B。不过对我来说,寻思这中间的断裂和化学作用也是一种乐趣。每个写作者首先也是读者,如果不是因为在阅读中得到的快乐,大概没有谁会愿意走这样一条“荆棘之路”吧。
科幻奇幻只是“外衣”我写的是现实主义小说
晶报:能说说你的文学启蒙吗?
默音: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而且是在云南的小县城里,所以即使我很爱看书,但那个时候能看到的书真的不多。家里订了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和《科幻世界》,这是开启我文学想象的两本刊物。对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16岁时投给《科幻世界》的,还拿了1996年的“少年凡尔纳奖”,这是杂志社自娱性质的校园科幻奖(笑)。
晶报:初涉文学之路,你以科幻小说起步,你喜欢哪种风格的科幻作品?
默音:这个很难一言概之。可能我喜欢的科幻都有点暗气质,例如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文奇的《天渊》《深渊上的火》,西蒙斯的《海伯利安》。这些故事里,人类只不过是宇宙诸多高等生命形态的一种,并不比其他生命更高级。作者们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他们的悲悯情怀则有如不间断的针刺,刺激着读者的神经。我也喜欢刘慈欣和韩松的小说,两位作家的气质可以说是迥异的,却都写出了让我着迷的作品。其实纯文学作家也有许多爱写科幻题材的,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过她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是科幻小说。
晶报:写过科幻和奇幻等作品,接下来你会在创作上突破自己吗?
默音:无论是科幻还是奇幻,只是一种写作的方法,其实我一直写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有时候有科幻或者奇幻的色彩,但本质上是现实的。作为写作者,当然希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写得更好。新的小说刚开了头,这一次没有奇幻元素(大概)。
晶报:你有这么多身份——编辑、译者、作家,平常该如何分配它们呢?
默音:事实上成为编辑之后只翻译了一本书——哲学家鹫田清一的《京都人生》。之所以给人一直在翻译的错觉,是因为有些书再版了,做了修订。例如《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和《家守绮谭》。现在基本是在夜里和周末上午写作,我也试过每天早起写一点,但天冷实在起不来,就放弃了(笑)。留给写作的时间确实不多,何况还想多看看书。
晶报:江湖传闻你喜欢喝酒,喜欢到怎样的程度?
默音:是从品尝的意义上喜欢。因为酒这东西是有文化和风土的,例如日本酒有不同的杜氏(酿酒师)流派,又譬如黄酒的不同品种在甜度和口感上有巨大的差别。所以,我要是自己喝酒的话,会是一个比较挑酒的人,会根据当天的心情选对应的酒。不过和朋友一起喝酒就无所谓了,因为一群人能聚在一起喝酒本身就是很开心的事。我虽爱酒,但不嗜酒,更不会每天喝。我写小说的时候不喝酒,必须保持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