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译作
来源:北京青年报 | 徐昕 2017年12月07日0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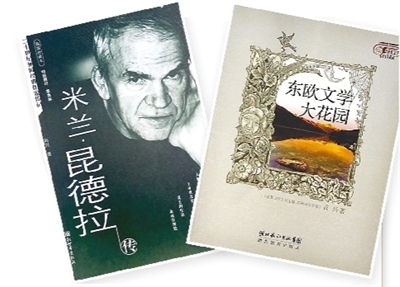

◎出题者:徐昕
◎答题者:高兴
◎时间:2017年11月27日
◎地点:《世界文学》编辑部
人物简介
高兴,男,生于1963年,诗人、翻译家,《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著有大量译作,出版有《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东欧文学大花园》《忧伤的恋歌》等专著、诗集和随笔集。主编“蓝色东欧”译丛,向中国读者介绍大量中东欧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
采访手记
第一次见到高兴,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一场中国-芬兰文学沙龙上,高兴是中方主持人,带来了很多中国作家,其中有大腕儿,也有几位并不太知名的年轻作者。在台上,他非常卖力地推介着每一位作家,不让一个人受到冷落;在会议间歇,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圈读者,他十分耐心地跟每一位粉丝进行交流,就像一位兄长,仔细地照顾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
高兴最著名的头衔,是《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对于国内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世界文学》绝对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杂志,它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正如高兴所说,如果北岛、多多这些诗人没有从《世界文学》上读到波德莱尔的诗,如果莫言没有读到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阎连科没有读到卡夫卡,他们的写作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初冬时节,我走进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文学》编辑部采访高兴主编。因为已近2017岁末,我们这张“人文问卷”的话题自然也就从这一年读过的书开始说起。
1 2017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一年里你读了哪些书?
我每年会读五六十本书,大多围绕着专业。这一年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比如捷克目前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赫拉巴尔的小说。今年我对国内正在推广的诗歌截句比较感兴趣。所谓截句,就是两三行的诗,但这些诗比较有爆发力,能一下子抓住人心。诗人北岛力荐这种诗歌形式。我比较欣赏的诗人像西川、欧阳江河、树才、朵渔、戴潍娜都出了截句选本。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觉很轻松,因为每一段都很短小,但每一句都带有高度浓缩的思想或情趣,所以很愉快。
2 能不能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三位作家?
如果要说最近比较喜欢,排在第一的是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第二是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第三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我特别佩服马洛伊·山多尔的叙事能力,觉得他是位拥有叙事魔力的作家。他有一部作品叫《烛烬》,余泽民翻译的,故事似乎很简单,在一对老友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展开,但它能牢牢地抓住你的心,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一本书是很自然的事,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时间推移,现在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我们读一本厚书往往会不停地被打断,但是读马洛伊·山多尔的小说时,那种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又回来了。
这几年我在主编一套叫“蓝色东欧”的译丛,今年看了赫拉巴尔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有一部叫《严密监视的列车》,是一部特别震撼人心的作品。我特别迷恋的是他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对语言的熟练运用,我把他称为“语言魔术师”。他能把日常的东西营造得那么有趣、那么迷人。他小说中的人性丰富、复杂,总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小说中的模棱两可是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因为文学不应该成为绝对的、黑白分明的道德评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他只是呈现,把生活中最迷人的,同时又是最幽微、最复杂的一面呈现出来,并且提炼到诗意的高度。所以翻译赫拉巴尔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在捷克语中赫拉巴尔肯定更加迷人,我们能把他百分之二三十的魅力传递出来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3 如今很多人都掌握了外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不要看翻译过来的作品,要看原版书。对此你怎么看?
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原文来阅读,但是能够完全领略原文魅力的人在中国恐怕还只是少部分。用汉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汉语表达方式所呈现的魅力,又是原文没有的。比如我们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读原文和读汉语译文是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两者都是不可替代的。
现在总体来说,热爱文学的人在减少。我们年轻的时候,文学生活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但现在生活如此多姿多彩,有那么多诱惑,有那么多其他乐趣,所以人们的兴趣是分散的。
4 你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罗马尼亚语专业毕业的,学这门语言是你最初的理想吗?
对。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比较单调,能够成为记忆中闪光点的,是那时候看过的外国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我看到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这些片子的时候,是很受震撼的。在那个相对单调灰暗的年代,在一部外国电影中突然看到一个穿着泳衣奔跑的姑娘,视觉上是会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力的,《沸腾的生活》中的这个情景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一回我和一些作家谈东欧文学,好几个人不约而同谈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看过的罗马尼亚电影。东欧情结就像种子一样,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后来有机会参加高考,而且可以选择专业的时候,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学罗马尼亚语,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我自觉的选择。
5 你现在还在翻译小说吗?
做编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己做翻译越来越少了。现在主要是翻译诗歌。(问:是因为篇幅比较短吗?)这是我的兴趣。我自己也从事诗歌创作,写作比翻译更能吸引我。做文学翻译会越做越惶恐,越做越知道它的艰难和无边无际。相比之下写作则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6 你最满意的译作是哪一部?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梦幻宫殿》,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梦宫》。因为我自己完全沉浸进去了,完全被这部作品吸引了,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翻译状态——翻译一部作品,你自己首先要被迷住、要被打动。文学翻译是一个被打动、被激活的过程。
7 很多人都说翻译是个辛苦活,你觉得辛苦吗?辛苦在哪里?
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常常会为了一个句子甚至为了一个词绞尽脑汁,经常半天在跟一个句子搏斗。翻译就是要找到那个最恰当的词、最恰当的句子。我们翻译的东西有很多并没有达到那个最精准的地步,如果有译者说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缺,那绝对是可疑的,是不可能的。
8 你觉得译者的收入怎样?
这是我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译者从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无论是从学术评估——在高校里翻译作品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还是从奖励机制,以及稿费标准来说,都没有体现出对译者起码的尊重。
最近几年,《世界文学》大幅提高了稿费标准,这是对译者劳作的尊重。翻译稿酬提高之后,很多译者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感到了这种尊重。另外现在也慢慢有一些颁给翻译家的奖项了。
9 你会关注读者的评价吗?如果看到苛刻的批评,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是特别感激的。我当然关注读者的反应。有人说一部好的作品可以完全不在乎读者,甚至可以把它放在抽屉里。但我想既然拿出来发表了,就应该关心读者的评价。我很关注那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比如做杂志就是一种遗憾的事业,每期做出来都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问:读者过于苛刻的批评会不会让译者背上心理包袱?)
自信的译者是不会背上包袱的。译者、作者的自信心很重要,自己要有底气。真正有经验的人会知道,要达到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
年轻时我对翻译的要求更苛刻一些,现在反而越来越抱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文学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影响和触动。中国有好多阅读者和写作者都是在误读中成长起来的,可即便是误读,它也产生了影响和效果。再比如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他翻译过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歌,他不懂汉语,是从其他语言转译的,用学术的眼光来看,庞德的翻译充满了谬误和误解,但即便这样的翻译,依然激起了一大批美国作家和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激起了大家对东方的关注。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甚至同意诗人树才的一个说法,一部好的作品,是经得起翻译的,是再怎么翻译都翻译不坏的。
10 你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对翻译这个工作的冲击?
很多人觉得是一种挑战,是对翻译这一行当的威胁。但我参加过一个活动,里面有一个环节:有六首诗,其中五首是作家写的,一首是人工智能写的,让读者判断哪首是人工智能的作品。大家一看就能挑出来。人工智能写出来的作品最缺失的是内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一缺失,文学的气息就没了。另外人工智能也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很多只是利用软件的拼贴。
(问: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以后,有没有可能也会具有情感?)
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但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有人说,纸质书很快会消失。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电子阅读回归纸质书阅读。当我们手捧一本书的时候,跟我们面对电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读书是一个整体行为,除了目光和文字的接触,手翻动带有墨香的书页,也构成了阅读的一部分。
11 除了看书之外,平时你还有什么爱好?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独处,同时又十分喜欢行走的人,但是现在苦于事情太多,我的行走计划总是没法实施。我喜欢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不是工作的原因,我愿意去当一个漫游者,我希望穿越到18世纪。因为出差的缘故我到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比如以色列、伊朗、波黑、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等等。我在捷克待过一个多月,完全是自由自在、独自漫游的状态,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压迫。
12 走过国外这么多地方之后,你最喜欢哪里?
我喜欢波兰的克拉科夫,说到这座城市,我会想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她的家乡就是克拉科夫,一座具有中世纪魅力的地方,一个你完全可以从容地、缓慢地来漫步的地方。这个城市并不大,但那种中世纪的气息特别迷人,有很多古老的教堂、街道和集市广场。那种从容缓慢的节奏特别吸引我。这样的城市在欧洲挺多的。布拉格我也挺喜欢,但相对来说布拉格比较商业化,它被太多的人关注。即便如此,布拉格依然是迷人的。要从城市的美丽程度来说,布拉格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克拉科夫不像布拉格那么引人注目,它还处于一种比较宁静的状态。
我们往往会说到国外的城市,其实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的城市。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丽江、大理。再比如我的故乡,我是在一个水乡长大的,这个水乡叫同里。小时候身在其中没有任何感觉,现在过了那么多年再回去,才发现原来是那么迷人的一个水乡。故乡的魅力是长大之后才意识到的。
13 12月10日诺贝尔奖就要在瑞典颁奖了,你如何评价今年的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当然是个优秀的作家,《世界文学》不止一次介绍过他。他有特别迷人的作品,比如《长日留痕》——当初我们在介绍这部作品时把它译成《残日》。这可能是他写得最棒的一部小说。但是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石黑一雄并不是一个作品特别整齐的作家,不能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品。
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特点是永远出人意料,而它的好玩之处也正在这里。那些评委挺会玩儿的,最绝的就是去年。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为美国文学抱不平,我们一直觉得像菲利普·罗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这些作家应该得奖了,结果诺贝尔文学奖真的颁给了一个美国人,但却是个音乐家。尽管有很多争议,但它还是成功地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我始终认为诺贝尔奖评委的阅读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获奖还是不获奖,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评判。但遗憾的是,很多读者是被奖项牵着去进行阅读的。
14 你觉得莫言之后,哪位中国作家可能在不久的未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近期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平衡,除了地域上的平衡,还有文学、政治、经济各方面微妙的平衡,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纯粹的文学奖项。目前在世界文坛上呼声比较高的中国作家有阎连科、刘震云、余华等等。
15 在一些活动场合见到你,感觉你会把身边的朋友都照顾得很好,在生活中你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吗?
这里面有一种尊重,尊重每一个个体,尊重每一个人。在一些场合,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我反而会比较少地去关注,我会关注一些现在可能影响力还不是那么大的人。包括在编辑部,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应该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人,哪怕是刚来的新人。一个团队应该有一种情感和心灵的温度。
16 如果当初不学外语,你现在大概会在做什么?
我少年的时候一直有军人梦。如果我没有上大学的话,我可能会去当兵。
17 对于2018年,你有什么愿望?
做杂志的人都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我现在已经在考虑明年7月的选题了。我希望明年《世界文学》能够办得更精彩一点。除了编杂志,2018年我个人还有写作和阅读的计划,有两本书要写,还要系统地读一些哲学著作。
在50岁之前,总觉得到了50岁就进入老年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都应该慢下来。在我老家有一种机制,到了55岁就可以“退居二线”。我一直希望自己55岁时能退居二线,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时间去做一些不带目的的阅读,做一些喜欢的翻译。另外我还要继续行走,明年我计划去英国、爱尔兰、日本这些地方住一段时间。跟其他国家相遇,跟其他文明相遇,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每次行走归来都会写出很多文字,行走能够激活我的内心,让内心产生无数奇妙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