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写作是我和我假想中的读者玩的一个游戏
来源:扬子晚报 | 蔡震 2017年11月21日08:19
[引言]
江苏是文化大省、文学强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江苏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学苏军享誉海内外。为了彰显江苏文学的实力和文学苏军的阵容,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下,去年江苏作协在北京推出了“文学苏军”10位领军人物,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今年江苏作协在南京又推出了“文学苏军新方阵”10人,他们是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羊、孙频。这10位均为创作成绩优异、创作成果丰硕的70后、80后作家。和老一代文学苏军方阵主要以小说为主不同,新方阵兼具小说、儿童文学和诗歌等领域,他们正在文学之路上赶超他们的前辈。近期,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连线这10位作家,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创作心路,听他们朗读自己的文字,感受他们作品的味道。本期推出的是作家——戴来
[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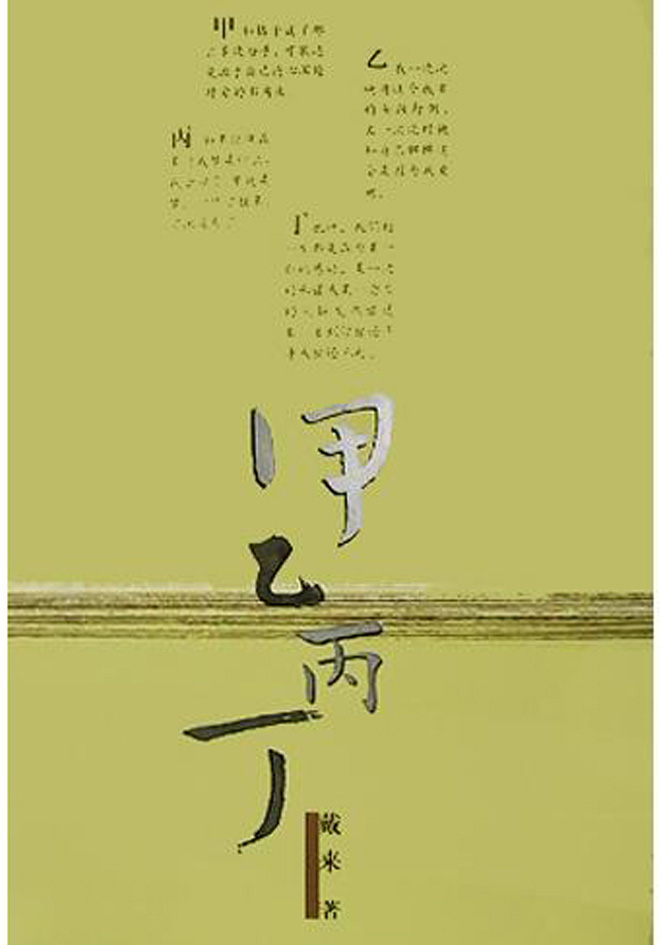
《甲乙丙丁》戴来 著 作家出版社
《甲乙丙丁》
近三年,我已经数不清和费珂之间有过多少次争执了,几乎每一次都是在我克制不住的狂怒中以一种暴力的方式结束。费珂惊恐绝望的眼睛让我心疼,也让我逐渐从中体会到了征服的快感,这真可怕。可更为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对此上瘾。暴力在升级,似乎只有更为强烈的暴力才能表达和化解我的愤怒。我一次次地将这个我爱的女孩打倒,又一次次对她和自己解释这全是因为我爱她。爱,让人失去理智,失去自尊,变得疯狂,变得愚蠢,变得连自己也不认识了。
费珂是个独立的有想法的女孩,和她交往越久,那种对她无能为力、把握不住的感觉就越强烈,可我最终让她屈服的是暴力。这是悲哀的。然而当对某个人的爱已经变成一种自己无力把握的依赖,你也许会理解我的。
最疯狂的那次我抄起厨房的水果刀就向她扎去,在费珂的尖叫声中,我看见她手臂那儿毛衣的颜色在变。起先只是一个点,但迅速在扩大,转眼间墨绿色的毛衣变成了黑色,一种奇怪的在运动着的似乎有生命的黑色,然后有液体滴落了下来,是鲜红的。
费珂首先镇静了下来。她拒绝我送她去医院,她用脚踢我,不让我靠近她。她把手臂靠沙发扶手垂着,她说,让我死吧,反正早晚会是这样的。
我手里的这把水果刀是我和费珂一起买的。我还记得当时费珂从刀架上拿起后还朝我比画了一下,做了个刺向我心脏的动作,没想到这把刀此刻握在我手里,上面沾着费珂的鲜血。
地上的红色和费珂的话刺激着我,我的脑子异常混乱又似乎特别清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必须得做点什么。我说那好吧,我们一起死吧。我把刀尖对着自己的腹部,在费珂的注视之下,毫不手软地扎了下去。
尽管我一再对费珂说我们是一对冤家我们不可能分开,但同时我也越来越怀疑自己真的能留她一辈子。我们恶语相加,我们互相伤害,我们越来越不介意把各自丑陋的一面暴露给对方。也许我们眼下做的只是把分开的理由铺垫到极至,让对方彻底绝望,让自己彻底绝望。也许真的只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才能结束我和费珂的关系,只有当我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停止纠缠她伤害她。
[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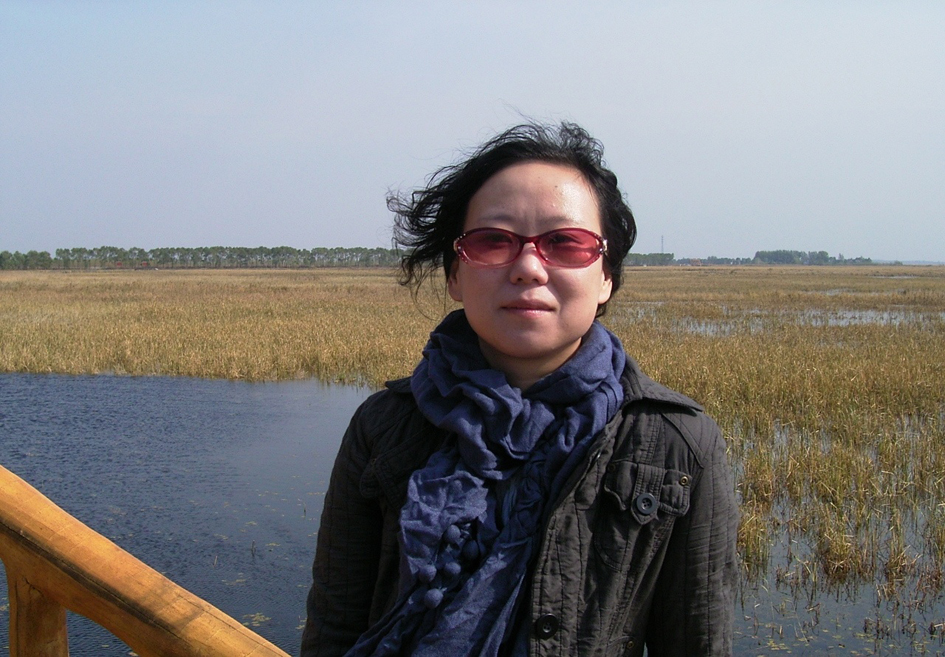
戴来 苏州人,现供职于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成英、法、德、日、意、俄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曾获首届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
[对话]
扬子晚报:你是何时开始写作的,触动你文学创作的动因是什么?你对70后作家代际划分,有何评价?
戴来:我曾经说过我开始写作是因为无聊。1996年去到河南新乡,没有朋友,没有工作,闲得发慌,除了每礼拜和我父母通个电话,原先的同学、朋友都没了联系,前二十多年的社会关系渐渐都没有了,就像是个注销了身份的人被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尝试写东西和当时的无聊、和需要让自己做点什么以便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同时也给家里人,尤其是我的父母一个交代,和给我的二十来岁时的不循规蹈矩的生活套上一件像那么回事的外套有关。
70后作家的写作有一定的共性,但特点各异,这样的划分有点偷懒,但已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
扬子晚报:作为苏州人,你嫁到了河南新乡,江南和中原,在两地间穿梭,对你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
戴来:年轻时在苏州,我可能完成的是不多的一点儿阅读,还写过一点儿诗,算是一种语言训练。而在新乡,我过着相对安静和简单的生活,有的是时间。有那么几年时间,我还真读了不少书。
七年前,我们举家从河南又回到了苏州。对我这样不太愿意和外界多打交道的人来说,其实在哪里生活都无所谓,反正一张书桌,一台电脑,然后把屁股放到椅子上,就是开始写作的全部物质前提。如果人生中没有特殊事件发生,阅读对一个写作者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扬子晚报:有评论说你的小说不像是女人写的,你常用男性的视角去描写,是挑战自我,还是追求一种趣味?
戴来:一个写作者站在自己的性别视点上试图对另一个性别世界做出窥视和理解(尽管这里面不可避免的带有自身的性别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件既有难度又好玩的事。事实上,用男性视角写作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的空间。
我始终把写作当成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在劳动着,这也是我爱写男性的原因之一。因为异性的世界和角度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让写作变成一件有意思的事。你成天在干一件有意思的事本身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扬子晚报:虽然写作年头不多,但你属于那种百发百中的作家,写一篇发一篇,是运气好,还是选题有目标?
戴来:1996年底我开始学习写作,写到1997年秋天时,大约写了有15万字吧,全是短篇,然后开始投稿。1998年第4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1998年这一年,我陆续在《人民文学》、《作家》、《钟山》、《江南》和《当代小说》一共发了10个短篇,全是自由投稿,我一个编辑也不认识,现在想想,还觉得带着梦幻的色彩。
我很幸运,碰到了好编辑,像当时《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原来《钟山》的唐炳良,《收获》的程永新。作为一个自由投稿者,和这些刊物打交道心里是诚惶诚恐的,我只是把稿子寄过去,好像连信也没附,并不抱太大的希望,结果他们采用了。还有《小说选刊》的冯敏,他选我的作品时,我刚开始发稿子,一点名气也没有。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素未谋面的编辑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的肯定建立起了我写作的信心。
扬子晚报:你认为一个作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生活和写作?你是处于一种放松的心态吗?
戴来: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我基本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不刻意,不强求。或者这样说,在生活上,我绝对顺其自然,谁也不要妄想去改变谁,包括孩子。而在写作过程中,我还是会为难自己和自己较较劲的,写得太顺畅了太快了未必是好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是我和我假想中的读者玩的一个游戏,我寻找难度,让我的写作不那么顺畅,让读者的阅读不那么顺畅,其中有着一种微妙的有趣的互动。但写完了,这些文字反而和我关系不大了。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走向,把它写出来就像是竭尽全力养育一个孩子至成年,成年以后的路,让其自己去走吧。对于写作者来说,有点像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把庄稼种好才是他的本分。其它的,管不了,也没能力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
扬子晚报:很好奇,听说你喜欢捣鼓软件,装了卸,卸了再装新的,这似乎与写作无关,此外还对什么感兴趣?
戴来:我小时候把家里所有的电器都拆开来过,包括在八十年代属于大件的电视机。这种好奇心令我父母无比烦恼,因为有些东西捣鼓开来不容易,复原起来更难。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觉得无聊的人,我喜欢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物,以写作的名义干一些和写作无关但我乐此不疲的事,我甚至把我们家所有的房门的前后两面用装修房子时剩下的油漆全画上了图案。但同时我又喜欢一个人玩,日新月异的软件和电子产品几乎是最好的独自就能玩起来的玩具。我曾经着迷于菜谱。现在喜欢看地图。尽管我是一个特别没有方位感的人,但那并不影响我在地图上神游。
[短评]
刘艳:戴来的中短篇小说,多为出色的篇章和佳构,颇具叙事的自觉、艺术自觉、精神向度和思想深度。作家以感性与智性兼具的笔触,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在现代社会男男女女林林总总并不复杂的生活故事和俗世生存当中,窥见人物内心和彼此之间的情感纠葛、生存焦虑与精神难题,看似写的是小人物,笔下装下的却是“大时代”。
岳雯:戴来将自己的个性、气质、做派,甚至是世界观、价值观中的一部分赋予了她的小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戴来制造。戴来的评论者无不勤勤恳恳地在她的小说中寻找戴来的痕迹,但戴来并不等于这一切的叠加,她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要更丰富、更复杂,坦率地说,她也比她的小说人物更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