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工人新村里的家族试验者
来源:北京晚报 | 张玉瑶 2017年11月20日07: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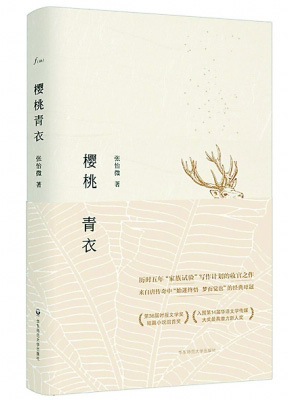

“‘樱桃青衣’是听心里的时间说话,蕉叶覆鹿是创造的本质。因为它确确实实生产了快乐,也确确实实是一场短梦”。这是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在她的新作《樱桃青衣》后记中的一句。
张怡微是80后作家群中的一个。少年时执笔写作,从“新概念作文”和《萌芽》中趟过来,后来走的是一条很稳的路:考入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去台湾读博士,做明代小说研究,如今又回到上海,做复旦中文系写作专业教师。出了参差不齐的十几本书,得了两岸三地七七八八的好几个文学奖。说是厚积薄发也好,天道酬勤也好,“屈脚蹲伏、弯腰缩臂”的耕耘,在这些年迎来了颇为丰硕的收获,尤其今年初一部描写离异家庭独生子女的长篇小说《细民盛宴》,以其对“这一代”年轻人特殊经验的介入式书写和百转千回蜿蜒曲折的心理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年中时,又有了《樱桃青衣》。
《樱桃青衣》是“历时五年‘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的收官之作”。原来有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张怡微曾在很多地方解释过这场“试验”,她尝试以此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却生活在一起的人”。《细民盛宴》写的是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少女袁佳乔的父母离婚后又各自再婚,于是许多原本毫无干系的陌生人闯入她的生活,成为“亲人”,并在一次次兼容温情与虚与委蛇的“细民盛宴”中,将日子延续下去。小说集《樱桃青衣》亦是如此,有结婚,有离婚,有再婚,有失独,有过继……对这样一群人和重组家庭的关注,或许与张怡微自己的家庭成长经历有一定关系,但她写一代独生子女的经验,却并不是站在一个经验重述者的角度,而是站在了一个完全的虚构小说家的角度——生活原本的面貌就是这样无序,这样充满不可预知和掌控的偶然性,由此生发的故事虽是一样的平凡琐碎不足道,却毕竟朝各个方向生出不一样的枝杈来。
张怡微在台湾研究了很久的“三言二拍”和《西游记》。笔下的故事,不难看出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子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市井生活的一大块黯淡皮革撕扯再撕扯,露出褶皱,露出褶皱里深藏的陈年污垢。然而污垢不全是丑的,它还暗示着油腻微温的人间烟火。和张爱玲、王安忆等几位最擅长写上海的著名女作家一样,生于上海又回到上海的80后青年张怡微,没有放过它特有的种种琐屑处,将这一代上海年轻人的经验接续上了这座都市的书写传统。但张怡微独特的补足又在于,她成长于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人新村,一个时尚光鲜的“国际大都市”的背面。由她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少被文学史敷陈的上海,但对上海来说,无疑是比符号更加真实的存在。
“樱桃青衣”和“蕉叶覆鹿”都是古传奇里的典故,是黄粱一梦般得而复失的怅惘,书名起得意味深长。表面平静的短短一瞬,于敏感的人,心里已过万重山,于写作而言,人生虽“未转头时皆梦”,却足以从中孕结出好的果实。况且张怡微说她想做那样一个以劳动的方式来写作的人,未来是可期的。
《书乡周刊》:“樱桃青衣”和“蕉叶覆鹿”这两个古代典故都表达了一种梦境般得而复失的体验。在这本集子里,你是想表达一种类似于此的情感和体验吗?
张怡微:“樱桃青衣”是《太平广记》里的故事,就是一个士子在梦境中经历荣华富贵之后又醒来,感觉到大起大落后的荒凉。为什么会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做《西游记》研究,发现《西游记》中所有的梦都指向死亡,这和唐传奇中关于梦的指向很不一样。黄粱一梦并不指向死亡,就像你说的,是得而复失。另一方面,“樱桃青衣”这个意象中涉及梦的内容又是极其世俗化的,香车美女、富贵功名,游宴欢会,很有烟火气,确实是比较接近我想表达的日常生活的样貌。
《书乡周刊》:这本集子是你“家族试验”写作计划的收官之作,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张怡微:“家族试验”实际上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一个“总结”,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想法。2014年我出版过一个单行本小说《试验》,里面收了两个小说。《试验》比较典型,写的是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却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团圆饭。当时我有想法,想找一些类似的故事,接近于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命运最终以一家人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后来出了《细民盛宴》,又在台湾出了《哀眠》,直至今年的《樱桃青衣》。有些“家族试验”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一小会儿,有些失败了反而令人怅然若失。
《书乡周刊》:“家”在你的写作中是个很特别的概念,不像传统中的意涵,即温暖的、庇护的、回归的港湾,而是像骆以军评价你小说时所说,是“变动的、凑合的”。你对“家”的理解是怎样的?
张怡微:“家族试验”可能写了一些特殊的状况,其实说特殊也不确切,许多问题也很常见:一些曾经来过的家人,不稳定的家人。年轻的时候,想到家会觉得是避风港,成年以后,反而想得比较多的是,我是这个避风港里的什么角色,我能为家庭承担什么,不管这个家的外延是什么、是不是原生的家庭、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自己需要承担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书乡周刊》:《细民盛宴》里浓墨重彩地写了父亲,《樱桃青衣》里也有好几篇写到了父亲和“失父”,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和意象。可以谈谈其中的意义吗?
张怡微:我有父亲,也有继父,用袁琼琼的话来讲,就是我有“两个父亲”,并且我们相处得真的还不错,这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的部分。我小说里父亲的力量肯定是偏弱的,不是可以无忧无虑依靠的,这可能是我的命运所致,但又并非表示我真实生活的父亲都不在场。两个父亲对我而言,永远是无言的山丘。我知道我选择写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误解,我只能在生活里对他们更好一点吧。
《书乡周刊》:你从小生长在工人新村,这是一个和一般文艺作品中的上海很不一样的上海形象。当它作为一个熙熙攘攘、带有某种社会性和阶层色彩的居住空间时,会呈现出哪些特别的世情?
张怡微:上海从工业城市逐步走向一个金融贸易、消费型城市。我们小的时候,许多人都是工人的孩子,纺织厂的、钢铁厂的、柴油机厂的、无线电厂的……现在这些厂都没有了,上海不再是一个到处是工厂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工人,所以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工人家庭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孩,爱读书的小孩,是很宽容的,父母们觉得家里有个孩子喜欢读书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读书总是对的。另外一方面,工人的自觉性又是很差的,他们其实很难总结好自己的一生,这是让我觉得心疼又同情的部分。
《书乡周刊》:你从小生活在上海,又去台湾读了博士,当时去台北读书是缘于怎样的想法呢?你在小说中也有关于上海、台北“双城记”的书写,这两个城市在你的写作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底色?
张怡微:当时台湾刚刚开放招生,就去了。因为我必须自己负担学费,我当时打了很多工,写了很多专栏,攒了一笔钱,只够去台湾。我没有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写那么多的文章,也是因为学费、生活费。一直到硕士,我都不算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我本科是复旦哲学系的,硕士是复旦中文系文学写作专业的。上海是家。
《书乡周刊》:你的写作一直“据守”上海,延续了海派新感觉小说、张爱玲、王安忆的脉络。你觉得你写的这一系列可以成为或代表一种新生代的海派文学吗?
张怡微:应该不会。我实在是不够格在这个脉络中。
《书乡周刊》:你在台湾研究明代文学,你自己写“世情小说”,古代的世情小说给你哪些启发?
张怡微:最大的启发是生活的力量。明清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让我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很匮乏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理解生活的方式。我非常喜欢李渔讲人情世理,非常幽默,也非常犀利。他有很多看生活、看人、看情爱的角度。冯梦龙也是,他编纂畅销书,必须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同时也是商人,所以他更接近消费文化,这一点和上海的文化结构倒是相似的。比方说,冯梦龙总是把商人写得有情有义,却把知识分子写得冷漠无情。这些故事基本都是萦绕在这些并不会说破的观念之下的。另一方面,通俗小说自有其生活力,我觉得开始研究之后,也刚好赶上我自己的年纪也慢慢长大,我开始学习理解了一些原来不会懂得的人、不屑去懂得的道理。
《书乡周刊》:你说世情是“市井中不被升华的真相”,你的小说里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和褶皱,常常会令人觉得某时某刻的情状确实是那样的。听说你经常会“素描生活”,那么是如何从生活本身的自然主义中跳跃升华出来,进入文学的呢?
张怡微:王安忆老师说,世俗生活不让人沉沦也不让人升华。我博士导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说小说又不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民族、国家,不同的取景框、测量尺决定了我们以怎样的境遇被抛入这个人世。有些基础工作,可能还是要先于找寻恰当的故事之前准备好。
《书乡周刊》:古代的世情小说常常是有一个作者俯瞰的视角,像《金瓶梅》。但你常常会从一些人物的特定视角看出去,比如《细民盛宴》里的袁佳乔、《哀眠》中的“我”等。有评论说,这些作为世情观察者的主人公有时会显得很冷酷薄情。你是怎样处理“人”和“世”的距离的?
张怡微:真的很懂人情世故的人、真的薄情的人,是不会去写小说的。写小说的人,在日常生活里,恐怕都不太懂人情世故。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不是一个多好的小说写作者,我也在学习,包括“冷酷薄情”,可能也是学来的。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人,对人也有期望,喜欢人的感情,容易被普通的感情所打动。我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站到可以俯瞰的高度,我也没有能耐驾驭真正的不幸,我是个很普通的通俗小说家,言言情、讲讲道理,做一些很普通的安慰、疗愈的工作。
《书乡周刊》: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作家作品?
张怡微:喜欢“三言二拍”、也很喜欢李渔的《十二楼》,很喜欢韦尔蒂、特雷弗,他们肯定有一些共性,比方对于烟火人间的关注吧。
《书乡周刊》:“家族试验”系列收官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作品正在计划中?
张怡微:去年入围了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因此今年上半年提交了一个小长篇《台北runaway》;明年上半年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后的博士论文《蛇足之辨》,讲到了明末清初的三部《西游记》续书,下半年还会出一本通俗文学散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