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所有的自传都在讲故事,所有的创作都是自传
来源:文学报 | 傅小平 2017年11月10日0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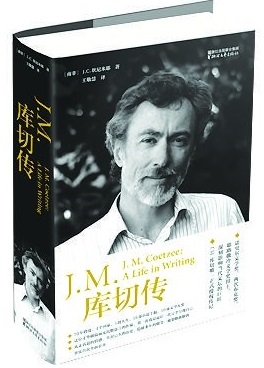
据说,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一生中独独对两样东西痴情不改:一是自行车,一是自传。
库切喜欢骑车进行长途运动,是他难得的公开的秘密,在南非开普敦期间,该城每年一度的自行车赛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他还是个修道士般勤奋自律的素食主义者,不喝酒、不抽烟,每天早晨伏案写作至少一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说到自传,1984年就任南非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主任,库切就职演说的题目是《自传里的真实》;200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自传”。
显而易见,如果说骑自行车让库切健康,并直至近年都保持堪为美好的体形、气质。自传则满足了他喋喋不休的自我倾诉。库切热衷于将自己隐在文字之中,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曾指出:“库切小说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根源于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价值观,在他的小说中,其个人的情绪到处可见。”他自己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陈:“所有的自传都在讲故事,而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
我们终于明白库切为什么不愿谈论自己
由此,想要真正了解库切,最好的,似乎也是唯一的途径便是阅读他的作品。也正因为此,近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J.M.库切传》的作者、南非传记作家J.C.坎尼米耶在该书前言中不由感慨道,对于像库切这样的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事实的情况是,库切的生平确乎很值得研究。这不仅在于如该书中文译者,库切研究专家王敬慧所透露,库切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私人空间的作家,他生活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谈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很少接受采访,有记者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动物保护机构才能得到采访这位素食主义者的机会。据说库切刚得诺奖的那几天,南非媒体都苦恼于如何想方设法采访库切而不得。
有据可查的是,有导演曾想把他的《内陆深处》改编成电影,并于十几年前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与他一起写剧本,但其间他说过的话还不到一牛车。导演说,你若问他一个问题,回答往往要等半个小时后。如果你问,你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库切总是不语,但千万不要以为无声就是默许,因为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后,他会回头来说:“不,这样不好。”另据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说:若是请库切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
实际上对库切的此等怪癖,实在不用惊诧。对于多少作家趋之若鹜的布克奖,他都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他两次获该奖,却未亲赴伦敦领奖。人们曾一度猜测他可能也会拒绝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很多年来,中国的出版社多次邀请库切来华未果,直到他终于答应参加2013年4月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有人预测他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话,没想到他竟做了将近15分钟的演讲,这诚然可以视为他对中国读者的礼遇,让人不禁联想到年轻时,他曾怀有一个中国情结:上世纪80年代时,他从IBM离职,确曾给中国大使馆写信说想到中国教英语,只是被阴差阳错地拒绝了。
无怪乎王敬慧感慨,这一次,库切坦然地把他的人生全部交给了他所信任的传记作家坎尼米耶,我们面对的将不仅是一部传记,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少见的出版事件。而以库切多部作品的中文译者文敏看,真正的库切和表达出来的库切、叙述出来的库切,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她认为从《J.M.库切传》的出版来看,库切是希望将自己的作品和真实的自我做一个切割。当然,从了解库切生平的角度,要说该书还有什么意义,或许不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在于如王敬慧所说,我们终于明白库切为什么不愿谈论自己。
从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的小说
不止于此,对于学习库切写作的作家,或热爱库切作品的读者,就像评论家德里克·阿特里奇说的,当我们去探讨库切的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联系时,或许可以比较清楚地窥看到,他的小说是怎样从他的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来的。
这样的“窥看”,不妨从读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开始。《男孩》和《青春》是库切两部各自独立而互有关联的作品,前者叙写主人公十岁至十三岁时在南非的孩童生活,后者是他大学毕业后到伦敦谋职的一段经历。
体现在《青春》这部小说里,库切本人的年龄和履历都跟书中的主人公相吻合,至于那里面的诸多细节是否也是作者所亲历,或许可以参照这本传记,但如评论家云也退所言,因为库切的人生和作品太一致,这本传记就少不了循环论证的嫌疑:拿人生来论证作品,又从作品来反证人生。
在《青春》里,库切写“他”19岁到24岁几年间的生活经历,一个南非大学生跑到伦敦做了计算机初级程序员,朝九晚五的公司职员,饭碗不用担心,却还是很郁闷。由于生性缺少热情,干不成大事也惹不出乱子。他也需要被爱抚的感觉,但性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生命的光辉,只是在吞噬时间和精力……
与此相对照,库切本人大学毕业后离开南非到了伦敦,和主人公约翰一样,做了一段时间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1965年他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文学博士,研究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荒谬派戏剧的主要代表塞缪尔·贝克特。尔后,库切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任教。1973年他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被捕后,离开美国重回南非。从1977年开始,库切开始发表小说,凭1980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他的名声开始越出南非。
而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夏日》里,库切索性写自己死后,传记作家文森特通过采访他人眼中的已故作家“库切”来构建一个多面、甚至不堪的自己。库切就如有评论所言,仿佛一个俄罗斯套娃深度中毒者,不断给叙事加括弧,括弧,再括弧,直到括弧本身成为叙事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所谓“自传体”的最大证据,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叫“约翰·库切”,并且里面的若干情节完全有出处,不但在库切以往的小说中均可找到相关情节,更可以直接对照库切的个人简历。
即便不是自传体,库切其他小说里的一些主人公也跟他个人的经历高度重合。《凶年纪事》里,主人公和库切一样,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年迈南美裔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里,年近七旬的女作家作品不多却很有影响,也有点像库切本人。若是参照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等等。我们甚至可以把科斯特洛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
饶有趣味的是,小说里科斯特洛获得了一项文学大奖,儿子陪着她去领奖,但她对这项殊荣很不以为然。她说,你们所授奖的这些书,过些年后人们将不再阅读,将被人遗忘。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应该减少留给子孙们的负担。关于颁奖仪式,她更觉得是多此一举,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这近乎是库切借小说人物道出的心灵自白。
某种意义上,科斯特洛正如有评论指出,是库切的另一个自我,人们读她的观点,也正是在读库切的观点。她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写我听到的东西。我是一个秘书,记录不可见的世界,我是许多个秘书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使命:一个擅长听写的秘书。对给我的东西,我无权审问或指责,我只是写下这些文字,然后去试验它们是否准确,我是否听错。“我有信仰,但是我并不相信它们。”
他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相信库切在小说里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却不能认为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相反,他和他塑造的人物之间,总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以女作家科斯特洛为例,别说她和库切年龄性别不同,按文敏的看法,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外在立场”,对世界的观察也远比她透彻。“库切的策略是让科斯特洛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忌顾地将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
或因如此,无论在自传体小说,还是别的小说里,库切惯于选择第三人称叙述。他之所以这样做,以这本传记所示,是因为他需要距离,距离带来安全和放松的感觉,以及审视自我的可能。诚如云也退所言,库切那个被始终压抑的“我”,也只能藉由另一个人之笔以“他”来表达,而且这个人必须跟他一样,有着“书写一个人物来让他不朽”的热切需要。比库切大一岁的坎尼米耶,恰好契合了他的这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结束全书时,坎尼米耶不由感慨“理解库切就是理解自己”,而坎尼米耶还没看到书的英文版出版便于2011年底去世了。
可以想见,库切或许如云也退所说,在坎尼米耶身上看到了一些令自己戚戚然的地方:他们各有各的写作人生,而这段人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也同时遇到了老龄和疾病的终极考验。库切回望自己的前尘岁月,也必然会感受到时间带来的复杂况味,他先后经历了多次沉重打击。第一任妻子菲丽帕·朱贝死于癌症,儿子尼古拉斯意外坠楼身亡,爱女吉塞拉在1989年罹患癫痫。种种不幸的遭遇,都让他苦行僧似的写作,带上了类似自我救赎,乃至自我疗伤的意味。
这般自我救赎的意味,体现在《彼得堡的大师》里,库切将尼古拉斯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夭的孩子巴维尔,他想象这位文学大师如何搜寻巴维尔生命最后几个小时里的行踪,以克服自己的悲伤。也因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是澄澈的,这种澄澈或许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它也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库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关系的书写,寄寓了他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对话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色彩。”
库切风格各异的作品,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都有着很强的隐喻性。就像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耻》,藉由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的遭遇,库切意欲探讨越界是否可能。无可疑义,任何事物之间都各有其界限,强行越界,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交流和沟通本身就预示着越界的可能,问题只在于我们得怎样遵守界限,又该怎样逾越界限?库切对此并没有给出解答。而他那些更具寓言性的小说,无论是《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还是近年的《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多元思想的呈现。
要阐明库切的思想无疑是困难的,相对可行的方法无过于把他从思想的云端拉回到地面,从而引发公众对库切的兴趣。浙江文艺出版社围绕《J.M.库切传》一书在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宣传,分别以《J.M.库切:当然,我不吃肉》和《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自我修养与成长》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用意。评论家李庆西说,读《J.M.库切传》最深刻的感受,在于能读到库切无论从自身人格,到哲学认识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修养。“从这部传记,还有库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聪明,不仅聪明,还特别刻苦,有了这两项,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库切。”他所说的这个库切,当然不只是作家库切,还有作为思想者的库切。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一章里,科斯特洛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就跟记者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在文敏看来,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