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陈雪《摩天大楼》——关于人性的隐秘拼图
来源:文艺报 | 石一枫 2017年04月28日0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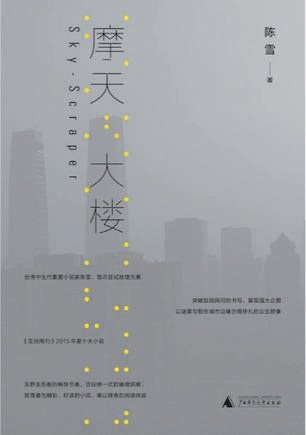
摩天大楼在现代城市中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发区域”,这种地标性建筑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城市正在向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最强有力的证据,20世纪初叶的纽约、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东京、进入21世纪的北京和上海,甚至中国台北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莫不如此。站在这种充满弗洛伊德气息的巨大棍状物底下,渺小的个人会感到自己像一只乏力的虱子——但与大楼相关的人们又会不由自主地用它来标定生活,就像有一次我去广州,谈论起这个地方的雾霾状况时,司机指着远方的一座摩天大楼说:“还能看见小蛮腰啦。”我还看过一篇专门有关于摩天大楼的报道,里面记录了人类在这方面创造的许多奇迹或者笑话,例如一个城市有两座大楼正在兴建,为了争取“最高”的名头,其中一方需要在临近竣工的时候加装一节巨大的天线,另一方则认为这是无效高度。
事实上,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人类现在能够兴建并且正在兴建的雨后春笋般的摩天大楼,其实用价值比之于成本已经越来越弱了。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有可能是一种性价比极低的建筑形式。大楼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每升高一米,对于建筑强度的要求都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想让100层之上长出101层,它的代价也许大于另盖一座没那么高的楼宇。更何况还有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维护成本、运营成本和环保成本。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热情地追求大楼的高度——无论借助的是所谓的“行政力量”还是“市场力量”。也许摩天大楼已经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产物。
我想,陈雪的小说《摩天大楼》首先是基于这种象征意义的。大楼象征着现代社会,而且还是看似高效运转、实则荒诞混乱的现代社会。小说中的大楼虽然并没有达到台北101的高度,但也是地上40多层,地下6层,说起来算是蔚为壮观了。这样一座大楼除了可以作为人们工作和居住的场所,同样也构成了一个相当繁复的社会缩影。从一部看似是“悬疑小说”的写作方法上,大楼也为故事的展开与铺陈提供了足够宽阔但却相对封闭的空间——出现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中庭咖啡馆年轻漂亮的女老板,那么按照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模式,“侦破”自然要在这座楼里的居民之中展开。作者可以从容不迫,让每个与死者相关的“嫌疑人”或“线索提供者”悉数登场。这些人按照与死者的关系划分,包括她的男友、情人、男暗恋者、女暗恋者……按照职业又分成保险公司职员、房产中介、咖啡馆店员和大楼管理员……构成了众声喧哗的“罗生门”。客观地说,这样的设置并不算非常新鲜,读过《尼罗河的惨案》与《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读者对故事结构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陈雪的主要用心应该不在悬案本身的侦破过程上——这往往也是强调“文学性”或“思想性”的作品与所谓类型小说的主要区别——对所处理的人物进行相当程度的挖掘,对人物关系进行有所指向的整合,从而拼建出堂皇的摩天大楼下隐秘的人类生存图景,或许才是作者主要目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摩天大楼》视为法国作家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式的小说,只不过通过借用悬疑小说的形式,使这部作品在情节上变得更加紧密,让人充满好奇。在获得了摩天大楼先天具有的象征意义之后,那种隐秘图景对于现代社会的说明性也变得宏大、确定、有的放矢了。
那么陈雪试图拼建的,又是怎样一幅隐秘的图景呢?在不同人眼中,同一现象之下蕴藏的本质也是不尽相同的,可以分成两个方向:其一是属于“人性”的,它关乎人的欲望、孤独以及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其二是属于人的“社会性”的,它涉及到阶级、分工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再发现和再反思。我感觉,陈雪的兴趣也许还是更多地聚焦在第一个方向。书中人的内心纠葛与外在行为,往往来自于他们独特的人生记忆以及心灵困境,比如层层剥茧地剖析表面上的“万人迷”、咖啡店老板钟美宝时,陈雪将她的人生还原成了与继父、弟弟有不伦之恋,又在几个男人之间徘徊的“真实状态”,而钟美宝的尸体被打扮漂亮又化了妆,这个案情的细节,则揭出了她的一个情人有恋尸癖倾向。再加上还有咖啡店女店员对老板的同性爱慕,对男人没有兴趣却在女按摩师的调理下恢复欲望的女邻居等等一系列情节……可以说,陈雪塑造的是一群在现代社会中被压抑、扭曲,被按照诡异的方式重塑灵魂的人格样本。在很多作家的心目中,这是一条更加内化也更加本质化的写作方式,再打个科学的比方,它有点像是微观层面的核物理,研究的是原子内部的裂变聚变效应,而非在化学和传统力学层面上的物质作用——归结于个体内部但能量无比巨大。陈雪在“摩天大楼”之下挖掘出来的隐秘拼图,关乎人性中无法坦然暴露的部分,而恰因其无法暴露,小说中摩天大楼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才超越了通常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具有了令人震惊的文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效果已经相当充分地实现了。
而假如说能够对陈雪的摩天大楼稍作一点补充的话,我倒想在这里提及另一种对摩天大楼的表现方式,它来自一部老电影《马路天使》里的第一个镜头:从旧上海“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建筑物下摇,仿佛深入地下,由此进入了大楼之外的那个阶级的生活场景。这样的视角当然来自于前文所述的“第二个方向”,与第一个方向相比,不能说哪一种更有价值,但两个解读现代社会的方式都是客观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