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电影:无限地逼近“相”
来源:文学报 | 聂伟 郑大圣 2016年08月25日1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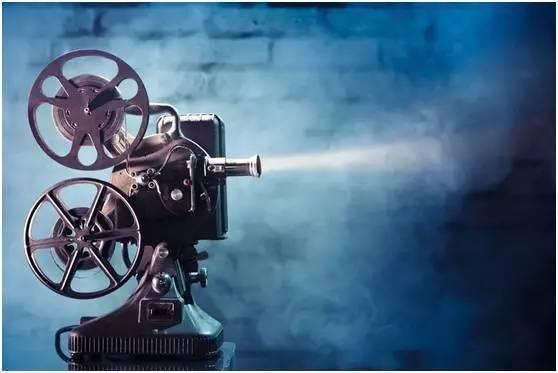

聂伟:青年评论家。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泛亚电影、当代华语电影和影视文化批评。出版有《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等专著,主编《电影批评:影像符码与中国阐释》《当代华语电影的文化、美学与工业》《历史光谱与文化地形:跨国语境中的好莱坞和华语电影》等影视评论集。
vs

郑大圣:青年导演。出身艺术世家,导演作品有《王勃之死》《古玩》《流年》及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等。很多电影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如《天津闲人》《危城》,以及根据茅盾先生的《蚀》三部曲改编的五部电影《春风桃李》《章台秋柳》《怀朴抱素》《江枫渔火》《霜天晓角》。近期,他还拍摄了根据已故河北小说家贾大山作品集改编的黑白电影《村戏》。
电影工业:需要“匠人精神”
聂伟:郑导你好。在进入访谈之前,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谈话场所处的宏观电影产业生态。我们知道,中国电影自产业化以来不断上演“速度与激情”,票房纪录屡创奇迹。但电影市场的乐观情绪在今年春节档之后频频经历“冰桶挑战”,第二季度的院线票房增速明显放缓,新的变数与拐点渐渐隐现。围绕这个问题,业界和媒体基本形成了普遍共识,那就是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还很不成熟。比如在创作领域,我们缺乏具有电影工匠精神的职业创作者,而电影工匠的人才厚度恰恰与电影产业的完善、电影市场的健全等指标构成正相关关系。
郑大圣:是的,电影摄制拍摄最需要的是很具体、专业性要求很高的职能岗位,比如说焦点员和轨道操作员。在以前的电影厂体系中,这个工艺链十分完整,师傅带徒弟,终身从事一项专业工作。一个人可以是非常资深的副导演,非常资深的场记,非常资深的摄影大助。以前大的电影制片厂都办过自己的技校,培养各个操作行当的专门人才,包括服装,道具、布置等等。
随着制片厂体系的崩解,专门的技术培训学校没有了,也不再是师傅带徒弟的有序传承,而是一些勤恳、聪明的人在行业淘汰竞争中自然升级,把兄弟、邻居、发小一个一个从老家带出来,很多时候,一个灯光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村的。
聂伟: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生态圈,以原来的家族、地缘、社交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电影产业村落。
郑大圣:中国对工匠从来是不在意的。我们的艺术史撰写天然的惯性就是忽略匠人、匠艺、匠作。
西方人在乎工艺,中国人不在乎。我们现在到博物馆去,从青铜到陶瓷再到丝绸,其实绝大部分是匠作。
聂伟:你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是如此。形制比较规整、老老实实用匠人方式来琢磨的作品,电影史里一般很少被重点提及,很多时候在整个篇章里面只有一段话。而那些被专章论述的作品,大多在分析那些灵光闪现的个性化作品,或者说作者电影。但是,在电影文化工程里面,这些职业匠人也是一笔一画、一砖一瓦的实干家。
郑大圣: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电影是技术要求最繁复的,它出现在人世间时,首先是一个科技魔术。它天然有一半是物质性的,极其依赖“器”,然后才有了艺术灵性和艺术表现这些“识”。这个对电影认知的前提,从来是被我们轻视的。
聂伟:如果以这个标准来重新理解电影,那么,中国电影史可能会呈现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从文学到电影
聂伟:我们来聊一下你最新的作品《村戏》。
郑大圣:《村戏》的缘起很简单。我一直和作家出版社有合作,作家社出版了《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白描式地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的河北农村生活,人物、生态和情境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意思,就拿来改编了。这些小说都很短,任何一篇都支撑不起一个一百多分钟的电影,我就选取了其中的5篇,作了改写量很大的自由改编。在剧本准备上,从小说文本到可以拍摄的剧本,我、编剧,以及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指导一起工作了一年半。
很多时候,小说激发出的导演的想象力,可能是原作者不在意的一个点。电影着重表现的部分,很可能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旁枝末节。所以,我每次都是用自由改编的方式去进行创作,《天津闲人》和《危城》也是如此,《危城》的改写量尤其大。我们只用了原小说里很隐晦的一个情节中的三四句话,将之扩张成一部电影。《村戏》也是如此。一部很短的小说里,一个人转述了他听说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几行字,但我们由此找到一个苗头,找到一个影子,让它重新发酵、重新生长。

我对小说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好的小说,从外看到里,再从里回到外,最后令人欢喜赞叹的,总还是文字的好。但文字不能直接转化成电影语言,导演只能自己体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这个过程不是借用和翻译,而是重新诠释和重新讲述。电影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是一次重新建构。
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很快就决定了要这个片子,也答应了我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我要做的是一个没有商业前景的电影。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肯定赚不了钱,我能做到的只是不让制片方赔钱。第二,我要拍一个黑白片。欧洲现在还有很好的黑白片拍摄传统,中国则很少,零星出现,且不持续。第三个,我不用明星,要起用非职业演员,最理想的是找到县级剧团以下、有表演才能的演员。
聂伟:江湖艺人?
郑大圣:对。为什么不找职业演员?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职业演员可以演出真实的农民。而且这部电影中有出演地方戏的要求。
在寻找演员时,我也提了三个条件。第一,要找到县剧团以下的演出团体。第二,故事里的所有角色最好来自于同一个团体。第三个条件最苛刻:这个团体经常演出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居所,就是他们生息繁衍的那片水土。只要是在母语环境、在自己熟悉的人群之间,在自己的家园上,谁都可以成好演员。
聂伟:要找到符合你“三合一”要求的演员,想来十分不容易。
郑大圣:我和制片人跑了河北省从南到北的9个县,看了9个不同的演出团体,有县剧团,有临时凑的班子,也碰到一整个村庄都能唱戏的“戏窝子”:村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吃完饭后就到村委会去唱戏,唱得很好。他们是很好的纪录片拍摄题材,但在这个人群中,我没有找到我要的面孔。我想找到一个“在路上”的戏班子,一帮能够覆盖影片所有角色的土著,他们得和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长在一起。
我们来回来去地找,从南到北,从邯郸一直找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往回找,最后走到一个叫作“井陉”的地方。那里地处河北与山西之间,在太行山里,地势险要,交通非常不便。正因如此,村庄虽然已然破落,但历史风貌还保留得比较完整。我们取景的几个村子里,现在还保留着明清的古戏台。
因为接近山西,井陉的风土人情跟山西十分接近。我们终于在那里找到一家唱山西梆子的民营剧团。他们常年在太行山两侧的村庄里演出,生存状况十分艰苦,每一年,他们都要带着铺盖在外巡演9到10个月,演满500场,才能维持基本生活。但他们的演员非常棒,至今保留着传统戏曲的很多绝活。这个剧团的观众都是中老年人。再过10年,不超过15年,台上台下的人都会老去的。
聂伟:到时就没有人看这些传统戏曲了。
郑大圣:年轻人都已经进城打工,没有人愿意学戏,学戏太苦了。很多时候,乡村的文化传承、人情世故,村民对历史知识的了解,都是用戏曲培养出来的。一旦脱离乡村生态,这种传播方式也就没了。
聂伟:去年,你根据茅盾小说《蚀》三部曲拍摄而成的五部曲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了连映,反响热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蚀》这部小说?

郑大圣:这是受了作家出版社的委托。茅盾先生其它的重要小说大多已经改编成电影,但这部处女作还没有。我读完小说之后发现,《蚀》中的荷尔蒙很直观,社会变革、革命与荷尔蒙、文学全部混合在一起。
聂伟:茅盾是左翼文学的巨擘。早期左翼文学的创作中“革命+恋爱”的模式还是很明显的,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社会精神氛围。
郑大圣:对。这部分是很动人的,但革命与情欲的交织裹挟不太适合电影审查,于是,我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从1928年到2008年,到2018年,甚至到2028年,始终都会是这样:所有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都会遭遇两层挫败:爱情挫败和社会生存挫败。没有经历这两个挫败,他们就无法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挺过这两个挫败,他们就完成了成人礼。茅盾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自觉地书写出了这个过程。而且,因为那时他刚开始写小说,技巧上还没有那么圆熟、稳健、深刻,但写作中的直觉非常敏锐。
聂伟:你将一部“私小说”拍成了公共电影。
郑大圣:其实还不够“私”,只能描写公共空间的部分。去除大革命、北伐等政治化元素后,这部小说表现的就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挫败感,这个话题在今天依然很有价值。
茅盾先生的文字让现在的我们读来哭笑不得:他写当年的年轻人怎样在城市里生存,如何谋求一个上进的位置,怎么遭遇挫折返回乡村。现在的年轻人依然在经历90年前年轻人经历过的挫折。近百年过去,我们在周而复始地面对同样的问题。
聂伟:现在的年轻人和90年前的年轻人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但是从更大的历史进程上来说,我们其实处在一个时间点上。
回到美学原点
聂伟: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背景。《天津闲人》里的主角绝不是大英雄,他的人生充满宿命感。《了凡四训》中,每个人物都奔向一个规定好的结局。当《古玩》的人物第一次出场时,我就想到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断魂枪》。身怀绝技的镖师沙子龙一个人寂寥地在月色里耍枪,有英雄末路的感觉,他在守护一个自己也把握不住的时代,最后只能用自己陪葬,口中念叨“不传,不传”。我注意到,你电影作品中很多角色的命运都比较乖舛,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处在一个历史的交界点,但他们在历史洪流里又不能发挥决定作用,总是身不由己,飞蛾扑火般地走向规定好的宿命。
郑大圣: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如此。我这次拍的《村戏》里,主角也是有特殊才艺的怪人,是一个会唱戏的疯子。
创作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越是自然选择的部分,自己越不知道从何而来。我每次都是很自然地作出了选择,但自己并没有察觉,也从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
聂伟:你电影里的美工是怎么找来的,好像他们做出来的效果,都挺符合你电影的意境追求。
郑大圣:我每次请美术设计,请摄影指导,请声音作曲,都是根据片子的特点来决定的,找不同的合作者。跟演员一样,各人有各人的戏路。

聂伟:《王勃之死》是你电影拍摄生涯中很重要的原点,我很喜欢。当时正是中国电影最低潮的年代,突然出来一部惊鸿般的《王勃之死》,有一种太奇妙的感觉。
郑大圣:当时没有人看电影。
聂伟:对。这部电影也成为现在一些年轻人拍摄艺术片时的标杆和模板。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可以用这么小的成本、这么短的时间,拍成一部有意义的电影。《王勃之死》给了很多艺术片创作者以启发。这部电影有很多情节犹如神助,后来我才知道此间你有过奇妙的经历。
郑大圣:拍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次都有神迹出现。拍摄《王勃之死》时,美术按照古画的意蕴建了一个临湖茅舍,我们不知道茅舍上空正好是西伯利亚陆鸥迁徙的路线,晚上一打灯,陆鸥有趋光性,飞来好大一群,我们就赶紧拍,这个景象完全是老天给的。这个戏我是前一天晚上写,第二天上午拍;中午写,下午拍。所以现在回头看来,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幼稚的。
聂伟:你用实验性的方法来做这部电影,也是在用一种巧劲。比如,我觉得《危城》就有点《小城之春》的意思。
郑大圣:我们在拍《危城》时,确实是按照昆曲的意蕴来表现人物的曲折、缠绕,这部电影里听不见的韵律是昆曲意韵的。我后来还请人把《危城》翻写成了昆曲。

聂伟:《危城》和《天津闲人》,哪一部作品更早?
郑大圣:我先用22天拍了《天津闲人》。第23天早晨,摄影机后面的人员没有变动,摄影机前的演员变了,换另外一组角色用20天拍摄《危城》。一共是42天。
聂伟:你这是比较早的IP转化工作,把经典小说改成电影。
郑大圣:其实,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多半来自小说,文学也不仅仅只有小说,如果我们把神话和戏剧都归在广义的文学概念之下,那么,没有一部电影可以逃脱文学的根源。全世界卖得最好的视效大片,它们的根源也来自神话。
电影从文学中寻找资源,是很自然的一个要求。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技艺,也是最古老的一种要求。现在的年轻人睡觉前追一两集美剧或英剧,或者到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和人类的祖先围着篝火听故事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恐惧、饥饿、寒冷,要度过漫漫黑夜,这时,人就需要一个寓言,需要一个解释:时间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从葫芦里来,我们从天上来……从篝火边到屏幕前,人类的基本需求一直没有变过。
再者,电影从诞生到现在才120多年的历史。小说以及更加长远的口头文学传统,是人类最古老而成熟的技艺,电影从这个系统里寻找资源,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